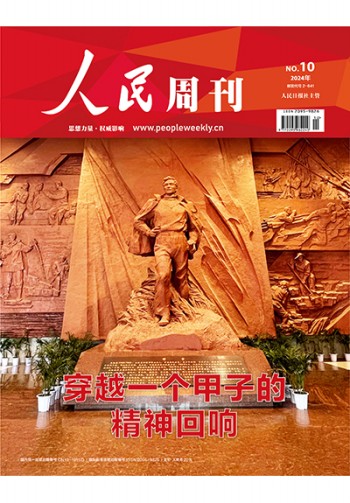2024年5月11日,傍晚时分的河南省兰考县,华灯初上,临近裕禄小学的一处餐饮街区,兰考县委原书记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外孙余音和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原馆长张继焦等候在餐桌旁,一如普通的兰考百姓一般。这是在纪念焦裕禄逝世60周年活动间隙,山东省淄博市焦裕禄干部教育学院副院长焦玉星发给本刊记者的留影。
随手拍下的画面,是一幅最寻常的当代兰考人民生活图景:街区人来人往,初夏将至,路旁支起冷饮、烧烤摊位,生蚝、小龙虾等水产早已成为这座内陆城市居民餐桌上的家常菜品,闲聊、聚餐的人群以不经意的姿态昭示着这方土地如今的安宁富足。鲜有人认出,身旁这一桌看似平常的来客,便是为今日兰考人民的安逸生活打下坚实基础的焦裕禄书记的亲友族人。
张继焦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岁月静好、物质充裕的兰考。在5月14日焦裕禄逝世6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已经退休的他依然忙碌在焦裕禄烈士之墓所在的焦裕禄纪念园,不辞辛劳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瞻仰缅怀的参观者。
“昨天早晨,我5点就到了。虽然已经62岁,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还是要发挥余热。”5月15日,张继焦接受记者采访,忆及焦裕禄在兰考的最后时光,以及自己作为曾继承徐俊雅遗产的焦家“养子”,与焦裕禄、徐俊雅夫妇之间剪不断的生命联结。在他看来,自己继承的最宝贵财富,是救活年幼病重的他、再度赋予他生命的焦裕禄留在兰考的不竭精神能量。
缘起1岁,情系一生
“2005年我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生的积蓄几万块钱。作为离休干部,又当过副县长,这点钱真不算多。大哥把我们7个召集到一起,把这笔钱分成7份。每人保留一份,其中的一份,给了张继焦。”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中,焦守云回忆了张继焦继承母亲徐俊雅遗产的往事。
这件事,张继焦记忆犹新:“老人家一辈子就攒了几万块钱。我对‘大哥’焦国庆说,我不要,咱对老人家也没尽多少责任。”后来,他把这笔钱捐赠给了一个有孩子的困难家庭,就像在他1岁多时,工资不高的焦裕禄访贫问苦来到他的家中,不仅坚持把奄奄一息的他送进医院救治,还慷慨解囊为家境贫苦的他支付医药费那样。
徐俊雅是2005年8月25日离世的,张继焦将这个日期刻在了脑海中,向记者讲述时脱口而出:“因糖尿病引起的复发病,在开封市淮河医院谢世,享年74岁。”
10岁左右父母相继亡故后,张继焦便几乎住进了焦家,“基本上生活在一起”。衣服破了,徐俊雅戴上眼镜,帮他缝补;生病了,徐俊雅擀一碗面条、打两个荷包蛋,帮他调理身体;就连找对象、盖房子,也是徐俊雅亲自操心操办……“都是经常现象,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张继焦已记不清是从何时开始,喊徐俊雅为“妈妈”,一切似乎是命运牵引,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焦裕禄的6名子女,都比张继焦年长,张继焦称呼他们为“哥哥”“姐姐”。“哥哥”“姐姐”长大后,相继离开兰考,到外地工作生活,徐俊雅晚年的许多时间,都是与张继焦夫妇相伴度过。
这种亲密关系,张继焦形容为:“虽然没有血缘,但就是母子无疑。”以至于徐俊雅离世后,张继焦仍然时常梦见她。近日,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为纪念父亲逝世60周年,也返回了兰考。张继焦见到“三姐”,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他把自己的梦境告诉“三姐”:“有一年,我梦见咱妈十几次……”
在张继焦心中,自己感受到的焦家家风,是毕生难忘的焦裕禄精神传承实践。“老人家对孩子的教育很严格。”他回忆,徐俊雅生前,每年清明节、5月14日等纪念日,焦家都会召开全员短会,母亲对子女讲得最多的话,是叮嘱他们好好工作:“你们如果工作干不好,人家不会说你们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
张继焦也记住了这句话。17岁高中毕业后,他从临时工干起,在建筑队搬过砖、返乡务过农,后来转为合同工,先后在县政府招待所、焦裕禄纪念园工作。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像“哥哥”“姐姐”一样,牢记“爸爸”的遗志,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精神风范,沙丘见证
在焦守云担任总监制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中,有一位名叫“小孙”的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全名为孙培谋,张继焦见过他。通讯员小孙,也是在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段,焦裕禄精神的见证者之一。
张继焦追忆,那时小孙跟随焦裕禄下乡,发现焦裕禄不时捂住肝部的位置,于是偷偷到县人民医院配了3副治疗肝病的中药。“3副中药,当时只需要花费几元钱。”焦裕禄却为此严厉批评小孙:“兰考人民还在逃荒要饭,你买这么贵的药,我能喝得下去吗?”
舍不得吃药,病情由轻到重;即使在病入膏肓时,焦裕禄仍然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治理内涝,兰考挖了一条通达山东省境内的贺李河。在河岸边和老百姓一起运土抬筐时,他肝疼得实在厉害,一头栽倒,滚到了河底。”对焦裕禄最后的岁月,张继焦讲述得格外细致动情。“送到附近最好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家一检查,说病得不轻,河南条件有限,最好去北京。”
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来自北京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的专家组织会诊,“结论是,顶多还有20天生命”。张继焦认为,焦裕禄在弥留之际、片刻清醒时的言辞,尤其能够体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他用尽全力拉着领导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死后,请党组织不要多花钱,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在1964年5月14日晚上9时45分,焦裕禄的心脏停止跳动,张继焦对这个时刻的记忆,精确到分秒。他和“妈妈”徐俊雅共度的时光,几乎从未远离这个时刻。徐俊雅晚年的住所,距离焦裕禄纪念园仅100米左右。“园里有长条凳供游客休息,老人家退休后,有时去那里一坐就是大半晌,到吃饭时才回家。”
如焦裕禄所愿,纪念园建在了兰考的沙丘上。张继焦刚记事时就到过这里,“距离当时的兰考县城有1华里远,站在焦裕禄烈士之墓的广场往县城一看,到处坑坑洼洼,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60年来,经济增长、城区扩张,“这个地方基本变成了县城的中心区域”。
张继焦亲历了兰考发展变迁的60年,也再不是最后一次面见“爸爸”时,在焦裕禄棺木前被父亲抱在怀里的2岁幼童。他说,若是能够与“爸爸”焦裕禄、“妈妈”徐俊雅再相逢,他会告诉“爸爸”和“妈妈”,兰考一年更比一年好,老百姓安居乐业,住房、交通、人们的精神面貌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此告慰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