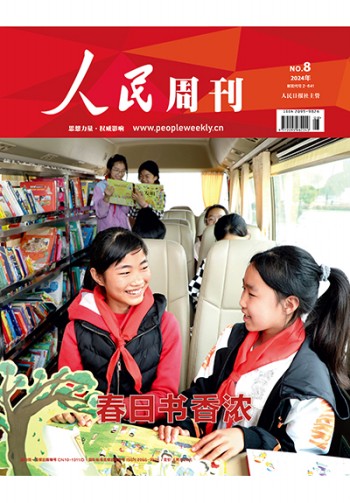徐悲鸿教育体系下主要发展的是中国画
林风眠教育体系下成名者几乎都是西洋画
艺术主张不同,艺术作品和培养出的人才也不同。
徐悲鸿主张借鉴西洋画,改良发展中国画,但一定是中国画,以期证实中国画有内在的发展潜力。
林风眠主张“创作时代艺术”,不管是不是中国画。事实上,林风眠培养的学生,发展的几乎都是西洋画。在林风眠的教育体系下,成名画家中没有一人是发展中国画的。
林风眠培养出的画家,包括和他关系十分密切者,有朱德群、赵无极、苏天赐、席德进,还有小有名气的闵希文、赵元扬、赵春翔等,以及关系较好的同事吴大羽等,他们基本上都是西洋画画家。朱德群、赵无极发展和丰富的也是西洋画。当然,他们也能画几笔水墨画,但只是用水墨、宣纸等中国的材料在画画而已,使他们立身成名的仍是西洋画。
吴冠中也是林风眠的学生,他是在法国学习的,他的画实际上也是西洋画。吴冠中回国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所画的几乎全是水彩之类。他后来画水墨画,用的仍然是西洋画的技术和理念,不过是用中国画的部分材料而已。其实他用的颜料、笔也是西方的,只不过用了中国的纸而已。中国画的线条功力在书法,他完全不顾传统书法,所以,传统中国画的线条,提、按、转、折,“侧锋顾右”“勒不得卧其笔”“努不宜直其笔”“趯须蹲锋”“策须斫笔”“磔者不徐不疾”等,他都完全不顾。他说:“笔墨等于零。”所以,他要推倒中国画的围墙。西方画以“目视”而不以“神遇”,中国画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所以西方画特别讲究形式美和视觉冲击力,而中国画讲究的是内在美,“切实之体”。吴冠中倡导形式美,即以“目视”而非“神遇”。所以,吴冠中的绘画理念也是西方的。
徐悲鸿体系下的画家,也都能画一些油画,素描尤精,但他的学生和其体系中的画家,发展的却是中国画,虽然他们的基础是西洋画。比如蒋兆和,虽然用素描的基础,但画出来的是中国画,而且对中国画有一定的发展。李可染毕业于国立艺专,曾为林风眠门生,后来又成为齐白石、黄宾虹的弟子,后来投到徐悲鸿门下。其走的是徐悲鸿的道路,完全用素描法,直接师法造化,但他画出来的是中国画。他发展了中国山水画,而不是西洋画。再后来的卢沉、周思聪、李斛、李琦、杨之光、姚友多、张仁芝、刘勃舒、韦江凡,乃至其再传弟子张凭、黄润华、贾又福、王迎春等,都是画中国画的。和徐悲鸿最亲近、也为徐悲鸿最赏识的画家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张大千、谢稚柳等,也都是中国画画家。当然,徐悲鸿弟子中也有西洋画画家,如吕斯百等,但很少。
国立艺专的延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及浙江美术学院所培养出的方增先、刘文西、周昌谷、李震坚、宋忠元、吴山明、冯远等新浙派人物画家,已不属于林风眠的教育体系,而是在潘天寿教育体系下的产物了。这一系中有一半教育思想仍是徐悲鸿的——以素描为基础,直接师法自然。
徐悲鸿强调“改良”,“改良”后仍是中国画
林风眠的“调合中西派”无主体、客体之分
林风眠系统中最杰出的画家,是画西洋画的,他们发展的是西洋画;其次是不中不西画(基础仍是西洋画)。徐悲鸿系统中最杰出的画家,是画中国画的,他们发展的是中国画。
这和林风眠、徐悲鸿二人的艺术主张不同有关。
林风眠1928年3月在杭州西湖组建国立艺术院(后改为艺术专科学校)时,为该校拟就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作时代艺术。”(《林风眠画语》,第68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调和中西艺术”,意味着中西是平等的,没有主体、客体之分。这也和林风眠的创作主张相同。林风眠在艺术上是“调合中西派”,笔者在拙著《中国绘画美学史》一书中,把徐悲鸿列为“改良派”,把林风眠列为“调合派”,把陈独秀列为“革命派”。革命派喜用“打倒”一词,其次是“革命”。如陈独秀说:“像这样的画学正宗……若不打倒,实是……障碍”,“首先要革王画的命”,等等。徐悲鸿则要把中国画“改良”,但“改良”后还是中国画,只是更好一些。林风眠则是“调合”,调合后只要好,不一定是中国画。他在《亚波罗》(月刊)上发表的《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中说,首先,希望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中西画,然后,要认识到中国画的长处和短处、西洋画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取二者之长,达到调合画家内部情绪的需求。因而,他要求学生既学中国画,又学西洋画,只有这样才便于取二者之长而调合之。(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571—608页)
他是以“中西艺术之调合”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所以,在他主持国立艺专工作不久,便合国画系和西画系为一系,曰“绘画系”。但绘画系的老师以及校内的老师,名望较高的基本上都是画西洋画的。原来国画系还有一个潘天寿,合并后(实际上是西画系“吃掉”了国画系)潘天寿的影响就十分小了。而且林风眠多次演讲、发表文章称“颓废的国画”“中国艺术衰败至此”。且学生一进校,无论倾向于何种画科,都得先学素描。林风眠等都称,将来画中国画也必须把西洋画画好。凡是优秀的学生,如艾青等,他又会选拔出国深造,赵无极、吴冠中后来也到法国留学,而学国画的学生自然不能出国留学。这样,优秀的学生都去学西洋画,而且志在西洋画。
林风眠本人也主要画油画,据傅雷回忆:“现在只剩一个林风眠仍不断从事创作。因抗战时颜料画布不可得,改用宣纸与广告画颜色(现在时兴叫作粉彩画),效果极像油画,粗看竟分不出,成绩反比抗战前的油画为胜。诗意浓郁,自成一家,也有另一种融合中西的风格。”(傅雷,《中国画创作放谈》,《傅雷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但傅雷又在《中国画创作放谈》中说:“融合中西艺术观点往往流于肤浅,cheap,生搬硬套……仅仅是西洋人采用中国题材加一点中国情调,而非真正中国人的创作,再不然只是一个毫无民族性的一般洋画家。”
林风眠的画,你说是油画,它又不是油画;你说是国画,它也不是国画。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调和中西”画。实际上是西洋画,因为观念、内涵、画法都是西洋的,只是用中国的宣纸而已。傅雷也说它“极像油画”。由于傅雷的鼓励,林风眠从此画这种“极像油画”的“粉彩画”。
朱德群、赵无极的画是油画,即西洋画,但借鉴一点中国画的情调。
吴冠中的画和林风眠的画一样,不中不西,这正符合国立艺专的校旨“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这“时代艺术”是没有围墙的。实际上,这种“不中不西”画是西洋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只是画在宣纸上而已。
60年后,吴冠中还要“推倒中国画的围墙”,实际上是用西洋画的理念和形式代替中国画,加一点中国情调而已。其实,他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时,这“时代艺术”本来就如此。所以,林风眠的“调和中西艺术”,也可称为“时代艺术”,它不同于传统艺术,倒有些同于西洋艺术。
如前所述,林风眠培养出的杰出学生,大部分还是发展西洋画的。徐悲鸿则不同,他的艺术是有围墙的,他要改良、发展中国画。他强调的是“中国画”。他说:“我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蒋兆和,《患难之交,画坛之师》,《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又见卢开祥,《为了祖国的美术事业——忆徐悲鸿先生》,《徐悲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把“国画”“中国画”提到突出地位。他不提“时代绘画”,更不提“调和中西”,而鲜明地标出“中国画”,如《中国画改良之方法》《论中国画》《新中国画建立之步骤》(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等。他更强调“中西画的分野”,专门著文《中西画的分野》,认为中国画与西洋画不但不能调合,而且也要与日本画分开,他说:“中国画与西洋画、日本画不同。现实主义每有困难之点,盖下笔偶一不慎,与日本画相差无几。”(王震编,《徐悲鸿论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