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这个春节出现在热搜上最多的人是谁,应该非钟南山莫属。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暴发初期,他一边告诉公众“尽量不要去武汉”,一边自己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挂帅出征;
他还曾多次前往北京,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座谈会,并第一个站出来直言疫情存在人传人,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在他的主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每天到医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专家组汇报省内重症患者的病情,并逐一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给予临床指导意见……
无论在广州、武汉还是在北京,84岁的钟南山一直为疫情奔走着。即使上了飞机,他也不肯休息,而是坚持工作,研究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并认真地作记录。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采访中几度哽咽,眼含泪光说:“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简短的话语,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定海神针”。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年逾八旬的逆行者有自信和勇气帮助武汉“过关”?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毅然挑起千钧重担?
与妻子因体育结缘
钟南山为疫情不停奔波的辛苦,妻子李姨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们能不能让他多睡一会?”
但陪伴了钟南山半个多世纪的她更深知,这个男人绝不会轻易下火线,“劝是劝不住的,因为他太在乎自己的病人了。”
李姨是周围人对钟南山妻子的称呼,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叫李少芬,更鲜有人知她曾是篮球国手。
1952年,16岁的李少芬通过选拔成为中国女篮首批队员之一。一年后,她随队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可惜的是,女篮打得很糟糕。回到国内后,周恩来总理提出让女篮姑娘们到苏联去学习球技。
在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女篮每年都要在苏联训练至少四五个月。除了训练,她们还到东欧各个地方打比赛,以赛代练。
其间,谢晋导演拍摄了以女篮为原型的影片《女篮五号》,李少芬还曾在影片中客串过欢送“球员”的群众。
渐渐地,李少芬的球技得到了提高,并成为国家队的核心球员。因技术十分全面,场上的五个位置,她均可胜任。此外,她的中距离投篮十分精准,而且还是用单手跳投。
留苏归来后,李少芬和队友们先后获得了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和1964年四国女篮赛的冠军。
打出了成绩的李少芬,自然成为其他国家球探相中的目标。一家由法国军火商掌控的篮球俱乐部找到了她,“法国人当时给我开出了很高的薪水,还许诺带我们一边打比赛一边周游世界。”但她拒绝了对方的邀请,一来是不想让国家好不容易培养的体育人才流失,二来是她在当时已和钟南山确定了恋爱关系。
钟、李两家原是世交,两家家长是医院的同事,但让两个年轻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体育。
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且成为一名田径队运动员。后来因为要参加全运会,为了加强训练,他申请到训练条件较好的国家队训练,这才有机会和同在北京训练的李少芬熟络起来。
自然而然,体育成为他们的共同话题,训练场也成了他们的约会地点。
1963年底,李少芬与钟南山在北京结婚。两人的婚礼简单而朴素,没有婚纱和礼服,连婚房也是体委安排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面除了一张床和简单的家居用品,再无下脚的地方,但李少芬对此毫无怨言,与钟南山过着幸福的日子。
1966年,李少芬从国家队退役。本可以留京做教练的她,因考虑到公婆无人照料,主动提出回到广东队继续打球。
直到1973年,38岁的李少芬正式告别运动员生涯,此后又担任广东女篮教练、中国篮协副主席等职务。1999年,她被选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杰之一。
如今,钟南山和李少芬的子女也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儿子钟惟德做了一名医生,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同时也是医院篮球队的主力;女儿钟惟月则继承了优秀的运动基因,成为一名游泳运动员,获得过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00米蝶泳冠军,还曾在1994年打破短池蝶泳世界纪录。
这样一家子,唯有用“强悍”来形容了……
“在我的生活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
名满天下的钟南山为人却十分谦虚,常常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大夫。”而这正源于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医术仁心。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儿科专家,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
当年,21岁的钟世藩考入中国医学界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8年的专业深造,他在博士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儿科医生(同期入学的40人只有8人顺利毕业)。
1946年,已在医学界颇有名气的钟世藩被任命为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同时兼任儿科主任。
3年后,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政府败逃台湾,想带着钟世藩等众多医学专家一起撤离。面对国民政府的威逼利诱,这位一身正气的医生不为所动,冒着生命危险拒绝前往台湾,选择留在大陆。
20世纪50年代,钟世藩首创儿科病毒实验室,这也是我国当时规格最高的临床病毒实验室。此前,他都是自费买小白鼠在自家顶楼做实验,儿子钟南山的医学启蒙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除了做病毒研究,钟世藩还坚持在每周二一早进行主任查房。在查房过程中,他会不时地向年轻医生们提问。为了应对他的提问,医生们会在查房前一天晚上开夜车跑图书馆查资料,还要找时间亲自动手为患儿化验检查。
其实,钟世藩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倒医生,而是希望年轻人能够重视基本技能,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他还要求,医生的病例记录要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时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时至今日,这个查房传统仍在延续着。
钟世藩踏实勤恳的科研及工作作风、对待病人的亲切态度,让儿子钟南山耳濡目染。
在钟南山的记忆中,父亲永远是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人。钟世藩晚年时,因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导致视力急剧下降,看东西非常费力。可他心系我国儿科诊断水平,即便是在眼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老人家坚持用一只手捂着一只眼睛,另一只手查阅大量国内外儿科资料,并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历时四年写出了《儿科疾病鉴别诊断》。因考虑到许多基层医生文化程度偏低,他在书中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文字。
钟南山很心疼父亲,劝父亲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写得这么辛苦,就不要写了吧!”父亲一口回绝:“不要写让我干什么?让我等死吗?”
该书出版后,反响空前,一连加印了6版,被广泛刊发给全国基层医院。后来,钟世藩得到1500元稿费,却丝毫不留,拿出700元给了帮自己抄书的一位医生,剩下的800元则用来帮助他人。
1987年,钟世藩临终前还在和钟南山讨论病毒相关的专业话题,并嘱咐他,自己死后千万不要开追悼会,节约大家的时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说,父亲的言行为钟南山树立了一生的榜样:“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
一家走出八位医学专家
与父亲钟世藩相比,母亲廖月琴及其家族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
廖月琴是国内护理学专家,也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曾被当时的卫生署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过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廖月琴刚当副院长的那段期间,钟南山常看见她去上夜校,读的书也都是关于解剖、肿瘤的。钟南山问母亲学这些干吗,当时已经50岁的廖月琴说,自己既然当了肿瘤医院的领导,总不能连肿瘤是什么都不知道。
令人惋惜的是,廖月琴在“文革”期间不幸去世,离世时才56岁。
而从廖家走出来的医学专家,不只廖月琴一位。
钟南山的大姨妈廖素琴是上海第一医院营养室主任,她的丈夫戴天佑是著名的肺科专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钟南山的表哥戴尅戎,是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的舅舅廖永廉是原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回鼓浪屿后成为厦门第二医院内科主任,曾在1957年发现福建省第一例钩端螺旋体病。他的妻子陈锦彩也是学习护理出身,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战地救护工作。待人热情的陈锦彩一生热心于鼓浪屿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和邻里红白事,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廖医生娘”。
也许是命中注定,廖氏家族中单是廖月琴这一系就有8位医生,而且个个都在医学界颇有建树,这才是实至名归的“医学世家”!
最近几年,人们经常讨论何为名门。真正的名门,不是家财万贯挥金如土,而是代际沿袭的精神财富,担当国民栋梁的格局和能力。
钟南山的家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家庭中汲取到无穷的力量与勇气,并反哺于他们深爱的小家和大家。
父亲曾对钟南山说:“一个人,要在世界上留下点东西,那他在世界上就不算白活了。”如今,钟南山对自己的后代说:“钟家优良传统有两个,第一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第二是办事要严谨,要实在。”
他们对后代的寄语,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其良好的家风密不可分。
钟南山继承了父辈良好的家风,传承了下去,并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力量。
今年的春节有些不一样。正是因为有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的人们,保护着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我们才能安稳度日。谢谢你们!
(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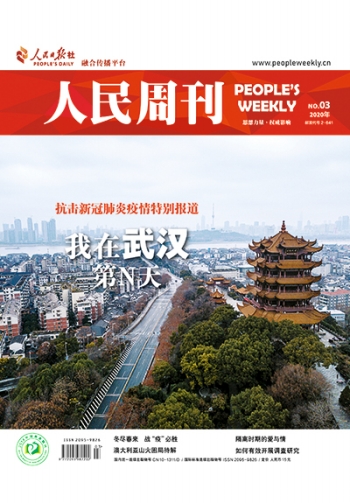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