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新闻工作者。《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
由于多在公共领域发言,近些年来我曾被不少媒体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时而还会入选一些年度榜单。我敢断定,最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词。
当时人们是多有期盼的。我也不例外。因为推崇艾米尔·左拉的缘故,在每年时事评论课快结束时,我还会给学生们播放电影《左拉传》,和那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一代分享《我控诉》里的清醒与担当,沐浴至今仍未褪去光芒的“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没有左拉的挺身而出,蒙冤的德累福斯定会死在牢里。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的中国与世界,都需要有公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良知与勇气。然而当有媒体记者把我贴上这个标签并且询问我对此“身份”有何感想时,我的态度则多少有些暧昧——既不公开拒绝,也不安心接受。
不公开拒绝是因为我乐见其成,希望有更多知识精英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共同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底线和理性。至于不安心接受,一是我自觉写作时瞻前顾后,做得很不够,自惭形秽;二是不喜欢被人贴上标签。我信奉“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只希望用自己概括自己的一生,而非某个外加的具有评价性质的身份。更何况,如读者所知,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这片土地上什么都可能缺,独不缺各式标签与“帽子戏法”。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短短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与“汉奸”“五毛”相提并论的坏词。而这也是我在持续几个月的方韩大战中,看到的最痛心的一幕。
这个社会还没有学会理性讨论,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被缩略成“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先是被廉价地滥用。任何在公共领域发言批评的人便成了“公知”。继而又有人创造了“母知”。
我时常感慨汉语被新话与脏话统治,任何美好东西在这个世界都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当我平素尊重的一些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用这样的词语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并自我撇清时,我看到这个社会,有股浊流,自甘堕落、无善不摧,又在自毁长城。对于一些人,现在不是抢占道德高地的时候,现在流行的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微博之上,处处枪林弹雨。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有人选择了自我了断,删微博走人,再次印证“劣币驱逐良币”;有人索性比坏,看看谁骂得更狠,一来二去,便有了“良币追逐劣币”。守不住自己,良币也变成劣币了。
对于前一种,我尊重拂袖而去的消极自由,但不支持“怨憎敌人枪法不准,索性自己吞枪自尽”的荒诞。知识分子必须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
至于后一种,关键还在于对独立精神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独立精神,不仅包括独立于威权与商业,独立于民众,独立于自己过去之荣辱,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观点,不以说服他人为目的,保持一颗自由交流的心。
其实,无论别人赞扬还是诋毁,你还是那个早出晚归的你。这世界,总有人会相信你,理解你,也总有人不相信你,不理解你。而时间终究有限,不要去纠缠比坏,不要易粪相食,只负责任地思考与讲真话。在“自杀”与“杀人”之间,在逃之夭夭的出世与争强好胜的入世之间,知识分子一人一座城池,可以通过守卫自己的理性与价值观从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我常以“以己任为天下”自勉,就是认为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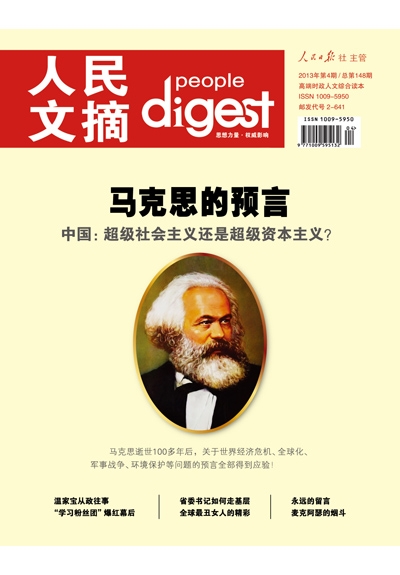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