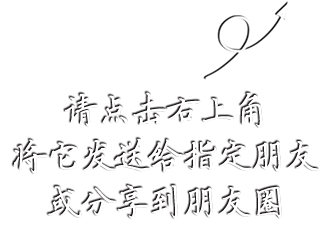|
图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动物搏斗铜贮贝器。 |
 |
图为江川李家山的虎鹿牛铜贮贝器。 |
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出土,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滇国”的真实存在。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上万件滇国青铜器出土,用直观而生动的青铜艺术语言再现了2000多年前滇国的历史与文化。牛作为滇国最重要的动物之一,几乎无处不在,农具、兵器、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品上都可见到它的形象。而贮贝器上的牛更是独树一帜,代表了滇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贮贝器是滇国用来贮藏海贝的青铜容器,类似于今天儿童的“攒钱罐”,其中贮藏的海贝是来自异域的珍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充当了滇国的“特殊等价物”,起着货币作用。贮贝器上最常见的装饰图像就是牛。
古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立牛一开始可能具有“盖钮”的实用功能,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品,从一头开始逐渐增至5头、6头、7头,多者达8头。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立牛铜贮贝器”是较早的,而同地出土的另一件“五牛一鼓铜贮贝器”,不仅立牛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还出现了“铜鼓”。器盖中央有一小铜鼓,鼓上立一牛,鼓旁四牛按顺时针环绕。中间的牛被“抬高”放置小铜鼓之上,其余四牛变成了“衬托”。这种变化使贮贝器盖上的立体装饰高低错落,富有空间感。李家山出土的另一件“五牛铜线盒”,器盖上也是五牛的造型,不过一大四小,“牛”的主题更为凸显。这种铜线盒在滇国也常被当作贮贝器来使用。从一定程度讲,铜鼓、牛、贮贝器,都是当时滇国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古滇国贮贝器上的牛还与虎、鹿等动物和谐共存,展示了滇国的生物多样性。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虎鹿牛铜贮贝器”,器盖中央雕铸一峰牛,沿边绕雕一虎、三鹿;器身刻几何纹、鸟、兽纹各一周,三器足为踞跪人形,以头颅与双手承托器身,构思颇为奇特。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西汉时期的“动物搏斗铜贮贝器”上,则出现了激烈的“虎牛搏斗”场景。该器为虎耳束腰筒形,下方四虎爪为器足。器盖中立一株无叶之树,树枝上有两猴、两鸟,树下是二牛一虎的惊魂搏斗。一虎绕树奔跑,左后腿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仅前爪着地,后腿腾空。显然,兽中之王与二牛搏斗中处在了下风。树上一猴抱树瑟缩,另一猴四顾欲逃,两只飞鸟在残酷杀气的催逼下,欲振翅逃离……动物搏斗的场面被工匠用戏剧化的场面瞬间定格。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剽牛祭祀铜扣饰”则表现了滇人斗牛、崇牛的习俗。扣饰最右侧的立柱上站立着一头公牛,柱侧11人正参与缚牛的活动。牛伫立不动,牛角根部系绳,穿在牛颈下结成活结。其他人或抱绳索、或抚牛背、或挽牛尾,其中一人被牛角挑穿大腿,倒悬于牛角上,手仍抓牛绳不放,发髻披散。还有一人倒于立柱下。11人头顶均梳髻,腕臂环戴成串手镯,腰间佩圆形扣饰,小腿束带,跣足。
如果让动物学家来辨认,滇国青铜器上的牛其实是不同的种类。最常见的是一种巨角隆脊的“封牛”。封牛即“峰牛”又称瘤牛,因为其肩背有巨大瘤状突起而得名,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牛背上隆起的峰是它最大的特点。滇国青铜器中还有牦牛、水牛的形象。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狩猎场面叠鼓形铜贮贝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时代在西汉。器身刻纹图案中就有一头牦牛立于树下,天空还有一只飞鸟展翅掠过。工匠们细致地刻绘了牦牛身上细密的长毛、巨大的双角、笤帚状的尾巴,让人一望即知。
晋宁石寨山还出土过几件铜牛头,从牛额头直到牛鼻子,都有厚厚的长毛覆盖,从形状分析,应该是牦牛。石寨山处于滇池之畔,西汉时期气候温暖,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牦牛应该不是本地的,很可能与巴蜀地区的一种牦牛有关。它们在青铜器上出现,说明当时的滇人对生活在高寒山区的牦牛已经有所了解。
199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件“鎏金二人缚牛铜扣饰”。该牛背上有“峰”,但犄角却是向下弯曲然后上翘,体型特殊。石寨山还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牛头铜扣饰,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是非洲水牛的形象,具体的种属及来源还待更深入的研究。也许2000多年前,滇国的对外交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