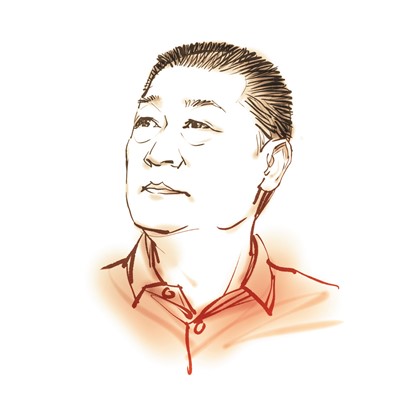从地图上看,那个位置应该在岑溪北岸,存仁堂附近。脚下是微黄的石板路,向西偏北方向延伸,一直缓缓向上,直到隐入阳光中的远山。据说,这段路通向徽商故道。
站在皖南古村落查济的十字路口,我对当地文友说,我们为什么钟情古村落,因为古村落有距离我们最近的生命记忆,有我们回访历史所能抵达的最远驿站。
从查济回来之后,我就放不下这个地方了,找了很多资料,并于40天后又去了一次,又走了几遍,聚精会神地住了两个晚上,聆听溪流潺潺,眺望月朗星稀,感受山林天籁。夜晚,脚步踏在千年前的街心石板路上,往往会想起“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之类的诗句。
我们不清楚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想象也许更接近真相。或许,这就是古村落存在的价值。或许,这就是我重返查济的动力。
一
查济保存了大量历史的痕迹——书院、祠堂、石桥、宝塔、民居……每一个古村落都是一座城市的种子,有的落地生根了,有的随风飘散了。而查济既没有扩张,也没有消失,就像一架停放在山坳里的踏步机,跟随地球走南闯北,时光的履带在它的脚下匆匆后退,过客的身影在它的眼里缓缓远去。历经1300多年风雨,它依然活着,并且继续焕发着青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同历史在查济亲近。似乎走到向西偏北的那条路上,就能邂逅查济的先人,沏一壶茶,聊聊过去的岁月。
在宝公祠,当地文友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查济的教育——话说当年,查济人秉承“由商致富,富而重学,学而致仕”的精神,宗族办学,诗书传家,但凡取得功名,由家族奖励田地,一家功名,全村共享。科举年代,查济村先后产生2名翰林、14名文武进士,近200名文武举人、几百名贡生、千余名秀才。这些人多数功成身退,回到查济办教育,行慈善,享受田园生活,为田园带来了文化的甘霖。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在华夏大地上,古村落并不罕见,为什么有的很快就被淹没了——或者被城市裹挟,或者被田野覆盖——而有些则保存得比较完好。这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人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养一方水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古村落的人似乎总是很淡定,你发你的财,我种我的田,你当你的官,我开我的店。你在豪华别墅运筹帷幄,我在自家庭院种花育草。
网上搜寻,古村落的人,寿命普遍较高。生命的质量并不在于大红大紫,惬意就好。
我喜欢古村落由来已久。在查济,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的几部——但凡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作品,里面都有一个古村落,比如《历史的天空》里面的高家庄,阡陌之上,阳光之下,小说人物高秋江的祖父、以耕读起家的高员外,在自己的庄园里开辟了一个乡村大戏台。秋收之后,大摆筵席,老人家笑眯眯地看着村里的农民喝酒吃肉,看着孩子在空地上尽情撒欢。还有《八月桂花遍地开》里面的桃花坞、《马上天下》里面的隐贤集、《狗阵》里的蛾眉镇等,最典型的是《英雄山》里面的其中坪,那几乎是一个独立世界。
这个发现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也就是说,我在描述宏阔的战争图景、欣赏金戈铁马的恢弘气势、礼赞英雄的同时,有意无意间总要在作品里设置一个古村镇,或藏在深山,或江河阻隔,在硝烟烽火中与世隔绝或者半隔绝,成为或明或暗的桃花源。如果说这些虚构的古村镇是梦想的产物,那么,在查济,我似乎看见了实体的轮廓。它既不同于我曾经到过的安徽铜陵和悦洲,也不同于我两次前往的陕西商洛漫川关,这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严重摧残。在众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中,我没有看到一处参与过战争的遗址,也没有听到一句关于战争的述说。因此我推测,当查济村的第一个建筑动工的时候,它的主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进攻或者防御。这种隐逸的理想受到了保护,并被继承下来了,使它在今天依然作为皖南最大的古村落群,成为一首历史写给今天的抒情诗。
二
“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环绕万户间。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关于这首诗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我无意考证。我好奇的是,此地不是崇山峻岭,也不是终年云雾缭绕,这么小小的山谷,这么矮矮的山岗,水是从哪里来的呢?当地文友说,查济村的西北方山脉里,有7个泉眼,涓涓细流源源不断。
查济的水来自查济,查济的水也养育了查济。在查济,你不用担心上游水清下游水浊,水会自我净化、循环再生。这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民间智慧。
在我看来,这3条溪流,才是查济村的灵魂,体现了查济村独特的品质,也似乎揭示了查济村旺盛生命力的来源。它们从不同的方向穿村而过,将错落有致的村落切割成3个大的板块和若干个小板块,同时也在6个河岸之间营造了遥远的错觉,本来并不太大的村子因此显得深不可测而又风情万种。初来此地的人往往会迷路,而迷路的结果是,游人熟悉了查济的大街小巷和一草一木。每一个来过查济的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查济,都有一幅查济村的清明上河图。
可以肯定,这3条小溪,至少有1300岁了,查济村的寿命有多长,它们的寿命就有多长。
三
古村落的时光都是缓慢的,从容不迫。在查济,时不时能够见到,小溪中间,桥洞下方,有几个农家女浣衣洗菜,说说笑笑,自得其乐。夕阳从水面反溅到她们的脸上,流光溢彩。在查济街上,我看见一个七旬老汉在编织竹制工艺品,问他收入怎么样,他回答,够用就行。见他满面红光,问他健康秘诀,答曰,知足常乐,就是最好的保健药。
什么叫诗意栖居,这就是。
不要嘲讽我们的梦想,每一个梦都是有来头的。
好几次,我都想继续往西前行,我非常看重查济的水,自然也就关注查济的山。我宁肯相信,查济周边的小小山林有着奇异的功能,那些葳蕤的草木,呼吸着日月精华,雨雪霜露涵养在根下,贮存在细密的泥土里,节奏分明地释放,流到山下。这些小溪一路歌唱,似乎在提醒人们,不要奢望我给你大江大河,不要希望我载着你们漂洋过海,就用我来煮茶酿酒,就在我的怀里荡涤心灵,让我陪着你们的时光缓缓流淌,生活是多么地美好。
第二次别离查济的那天早晨,我在潮湿的冷空气中漫步,走到那棵著名的紫荆树下,仰望这位500多岁的老人,我说,您老人家真好,活这么大岁数。晨曦微风中,我听到老树爽朗一笑说,到查济来吧,听我给你讲故事。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著有小说《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曾获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