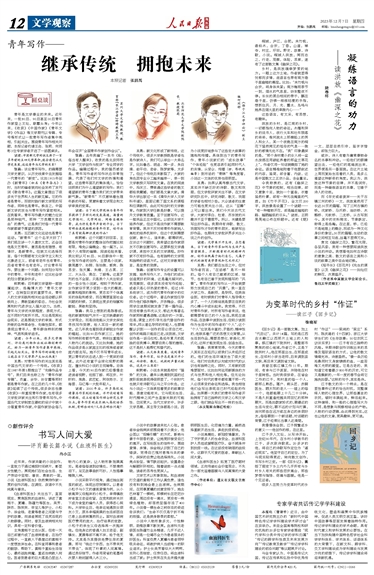青年是文学事业的未来。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甚至00后青年作家登上文坛,崭露头角;今年以来,《收获》《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作品》等文学期刊以专辑、专号等形式让一批青年写作者集中亮相,引起关注。围绕青年写作相关问题,本报记者约请王尧、张莉、何同彬3位专家学者开启了一场圆桌谈。
记者: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源于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文学革命。能否请您从文学史角度,谈谈青年与文学的关系?
张莉:谈论青年写作,的确需要文学史意识,从历史线索中去发掘每一代青年的“新变”。比如1915年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时,当时的编者就向社会发布了发刊词《敬告青年》。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新见解。它的作者是青年,而彼时践行新文学观的写作者,同样也是青年。换言之,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青年写作紧密相关。在我看来,青年写作最大的魅力应该是那种锐气,那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勇气,这是我们对每一代青年作家都寄予厚望的原因。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青年运动。“新青年”这个名字太好了!我们现在讲一个人喜欢文艺,还会说他是文艺青年,意思是他有理想、有情怀,是新青年。但就文化选择而言,每个时期都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前者有老年也有青年,后者有青年也有老年。讨论青年写作,要注意一个问题:如何划分写作中的青年、中年和老年?这比社会学的划分要复杂许多。
何同彬:百年新文学堪称一部波澜起伏、浩瀚博大的“青年文学史”,在转型巨变的重要节点,青年人的文学实践和相关社会活动都以积极向上、勇敢坚毅的姿态,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当然,青年与文学的关联程度、表现方式,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无论是观照社会现实,还是围绕文学的审美、形式所做的各种革命性、先锋性探求,都表现出青年人、青年群体特别的精神、气质和美学追求。
记者:今年以来,很多文学期刊、评论类刊物和出版社都创新形式,助力一批青年写作者集中亮相,引起文坛关注。青年写作的话题为什么能在当下文学界产生如此热度?
王尧:对青年写作的关注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收获》在1987年第5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我们后来也称之为“青年作家专辑”,苏童、余华、孙甘露等那时都是青年作家。在之后的几十年,《收获》延续了这个传统。很多杂志也像《收获》一样重视青年作家,也有很多文学批评家关注和引导青年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中就十分看重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每几年会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张莉:去年我编了一本书《耘:每当有人醒来》,收录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同学的作品。编辑过程中,我的强烈感受是,青年写作者的写作状态非常饱满,代表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渴望。这些青年面孔的集体涌入,恰恰说明我们为什么渴望新的写作:我们渴望新的青年力量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新气象。“新青年”不仅意味着生理年龄的年轻,更意味着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的变革。
记者:当下的文学现场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多样化的发表渠道,海量的文学报刊、文学网站、网络自媒体等,成为抒发青年声音的平台。当下有哪些表现抢眼的青年作家,创作出了具有较高辨识度的作品?
何同彬: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主要是对青年作家的整体创作把握比较有限,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从我个人有限的编辑、阅读经验来看,我比较认可80后、90后群体中一批女性写作者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家,像周嘉宁、孙频、张怡微、郭爽、陈思安、张天翼、朱婧、王占黑、三三、大头马、蒋在、丁颜等。这里罗列的也不全面,只是我个人关注较多的一些女性小说家。相较于男作家,女作家似乎更少受到一些大的潮流、叙事和框架的影响,更忠实于个体真实的体验和感受,而在需要直面社会问题的时候,又表现出更多的细腻和敏锐、果敢和坚持。
张莉:我马上想到的是陈春成。他的新意和锐气并不一定反映最新的文学观念,而是说他能从文学史深处寻找写作资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近几年我也看到很多新锐女作家的崛起,比如90后作家三三,她的写作特别有都市气质,特别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流动。又比如朱婧,她的作品很多是从家庭主妇的视角或者家庭内部去写。她不仅书写青年成长,更以青年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此外还有富于全球化视野的蒋在,擅长科幻小说的王侃瑜等。总体上看,今天的90后作家已经慢慢走进读者视野,包括丁颜、郑在欢、叶昕昀、焦典、武茳虹、阿依努尔、王海雪、马亿等一大批年轻人。
记者:2000年后,许多高校延请著名作家到校任教,并开设创意写作课程,设立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学位点。青年作家的成长纳入高校培养机制,有哪些好处?又存在哪些问题?
王尧:新文化形成了新传统,这个传统中,很多大学教授既是学者也是作家诗人,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比如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老舍、陈梦家等,太多了。但这个传统后来断裂了,大家的角色因专业分工越来越单一,单一到文学教授只写研究文章。在我的阅读中,冯友兰、费孝通这些学者的散文都给我震撼,他们都是文章大家。清华大学出版过一本《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年谱》,里面记载了国文系的课程和任课教师,由此可知当时的文学教育。作家到大学任教是好事,可以提升文学教育质量。至于创意写作,这一舶来品正在中国化。以前说大学不培养作家,但这不是说作家不需要教育背景。我并不反对将青年作家纳入高校的培养机制中,但这个机制需要创新,教什么,谁来教,都需研判。在谈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这些作家朋友不仅教创意写作,还要承担文学通识课,承担中文系的文学课程。好作家不仅有好作品,也有独特的文学观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这对文学教育而言,是宝贵的资源。
张莉:创意写作专业的设置可以发掘、培养写作人才,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观察到,很多原本没有写作经验,或者只是心怀热爱的青年,经过3年系统学习,成为同代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个过程中,著名作家担任导师为他们修改稿件,开改稿会,很多同学在读期间就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而没有像当年沈从文、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那样遭遇退稿,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课堂上的引导无法代替创作的艰辛。师从著名导师的年轻人,也要清醒认识到——创作的苦必须自己吃,创作的弯路只能自己走。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场马拉松,是经年累月的孤独的自我搏斗,需要自我心智的磨炼,这不是别人能帮忙和替代的。
记者:从文体角度看,谈到青年写作、青年作家,似乎总是离不开小说,而诗歌、散文、戏剧的声量比较低,这是什么原因?
何同彬:小说本来就是相对“强势”的文体,最早从晚清到民国的过渡阶段就表现得很明显了,个别时代也就只有诗歌可以与之平分秋色,这与小说这一文体承担着更多的叙事功能、表意功能有关,它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之间产生直接关联的可能性、空间更大。当代文学史中,许多文学思潮,其主导文体都是小说,因为小说更好地参与了这些宏大叙事的建构和传播。具体到当下的青年写作,青年小说家们的“成长故事”“个体经验”也更容易引起同时代人的共情,从受众、传播(IP、影视改编等)到市场的“青睐”等角度看,小说这一文体的优势也很明显。
王尧:如果认真考察当代文学,其实并不缺乏好的诗歌、散文和戏剧,但文学批评家关注不够,在文学研究队伍中,研究诗歌、散文、戏剧的学者也相对少些。大众读者的注意力可能也更关注小说,这从“豆瓣”上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谈古代文学,大家对李白、杜甫、苏东坡的兴趣并不亚于曹雪芹。所以,关键是要写出好作品。我期待有诗歌、散文、戏剧写作才华的青年朋友,能够写出好作品,也期待文学批评界多关注小说之外的创作。
记者:文学离不开生活,在您看来,当下的青年作家如何与生活产生紧密联系,不断探索时代的精神内核,创作出既属于他们自己,又属于时代的独有美学景观和艺术形式?
王尧:我们都在生活之中,但对写作者而言,“在场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自己敏感的区域、细节,也有自己善于发现和描写的“风景”。青年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发现自己的“风景”。我一直在大学工作,是教师,是导师。但我体会到,有时候我们对青年人指导得太多了,一个人归根结底是要在自我的内心搏斗中成长起来。我觉得,不仅对青年作家,对所有写作者来说,他都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我现在读作品,在故事中读到生活,但较少读到作为生活中的写作者的“个人”,这个“个人”应该是丰富的、矛盾的、精神性的,他联系着广泛的思想文化背景。从生活到作品,需要思想化、审美化、形式化,这样才能发现生活、创造生活。
张莉:我常常觉得,今天的青年人其实正在经历以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或对时代的认识也有独特之处,同时,又有新的困难要面对,比如如何运用新媒体的方式与世界和他人相处等。但无论如何,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属于那一代人必须承受的命运和选择。我也相信他们会写出表现自己时代经验的作品。如果哪一天我们的青年写作者开始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心和文学之眼,他们就会写出不一样的生活。
(本文配图由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