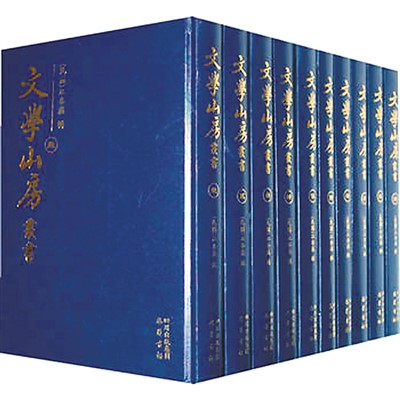江澄波老先生1926年出生于苏州,如今已97岁高龄。家中自祖辈起经营古旧书店,一生与古籍打交道的他,精于版本目录、修复鉴定之学,被誉为“苏州一宝”“书林活字典”。他所著的《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活字印书》《吴门贩书丛谈》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22年底,由江澄波口述的《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问世,并获评“2022苏版好书”,入选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他的人生经历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带着几分好奇,我们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走进这家小小的文学山房,采访了江澄波老先生。
文学山房,苏州城的文化符号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闹中取静的钮家巷里,有一家名为“文学山房”的小小书店。它位于苏州状元博物馆斜对面,玻璃门内,满屋的古旧书煞是引人注目。店门上方,暗红色的砖石上,7个金色繁体大字“文學山房舊書店”古朴大气,但却没有署名。了解书法的人能看出来,这是苏州书画家马伯乐的手笔。走进店里,文学山房三面都是高高的实木书架,各种古旧书排列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其中东侧靠墙的书架上,大多是线装古籍,每部书中夹有一张签条,上面写着书名、编号等信息,方便找书人翻检;正对面的书架上,多是各类大众文史读物;西侧靠墙的书架上,以苏州地方历史文化读物为主。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题材各异的旧时出版物。而进门左手边,有一张圈椅,那是江澄波的“专座”,他每天就坐在这张椅子上,等待四方读者和访客。旁边的一张凳子,便是为进店的读者和访客准备的。
我们闲聊起来,谈到“书房”这个话题,江老滔滔不绝。文学山房虽是书店,但也是他的书房。江澄波在文学山房出生、成长、学习、生活、工作。“文学山房里有我一生的记忆啊。”老人说。不过,这间小小的房子并不是最初的文学山房。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嘉余坊口创办文学山房书店,专门经营古书买卖,这就是最初的文学山房。创办后,先是赶上黄葆年在苏州创办归群草堂讲学,学子云集有购书需求;辛亥革命后,在苏官员离开,留下众多藏书,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在业内形成良好口碑。到1931年,江澄波5岁时,最初的店面已不能适应业务需要,于是书店迁往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口,地址是护龙街707号。新中国成立后,护龙街改名为人民路,文学山房的地址也改为人民路326号。到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文学山房改名为“公私合营文学山房”,仍由江澄波和父亲负责。1958年,文学山房成为苏州古旧书店下属的4个门市部之一。1961年,其他3个门市部撤销,只留下文学山房这一个,改称“古旧书门市部”。至此,文学山房的历史告一段落。
2001年,75岁的江澄波已经退休,家中经济状况不佳。为了攒钱供两个孙女读大学,他重新干起老本行,学习祖父白手起家,开办书店。由于原先的文学山房已合并,为免误会,新书店一开始定名为“文育山房”,地址是建新巷25号,经过几次变动最终搬迁到钮家巷现址,一开就是十几年。可喜的是,2012年,在广大读者和媒体的呼吁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江澄波的书店恢复了百年老店“文学山房”的招牌,让苏州从此多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符号。
谈及这些历史,江老如数家珍。脸上认真的表情里,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时光如流水的感慨。
下苦功夫,在实践中习得本领
1931年,文学山房搬到大井巷口时,店面是传统的前店后宅形式。江澄波就在店里长大,跟着祖父和父亲学习版本鉴定、装补修复、刻印校对等知识,也跟着祖父和父亲外出访书,学习做生意,逐渐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治学是没有捷径的,最要紧是下苦功夫。”回忆起跟着祖父和父亲学习古籍知识的时光,江老这样说。那时在店里,为了快速熟悉古籍书目,掌握经史子集的各种版本信息,江澄波用的是最“笨”的方法——背书目。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目是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创办江南官书局,莫友芝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潜心研究版本目录学,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被后人认为是版本目录学的扛鼎之作。江老说自己看这本书目,一开始是硬着头皮看,慢慢地有了一点心得。通过将书目与真书对照着看,他就记住了,并且能够背下来。背完一本,再换一本,长年累月下来,江澄波掌握的版本知识已十分丰富。
“光背下来还不够,还得抄。不光抄已有的书目,店里收到书,我自己也要抄列书目。抄写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不断巩固的过程。”江澄波说。其他知识,诸如版本鉴定、书版特征、纸张特色、鉴别真伪、修补修复、钤印、题跋、批校,乃至待人接物、写信回信等,祖父和父亲也都悉心教导。江澄波专心学习,下苦功夫一点一滴积累、领悟,慢慢成长。
除了下功夫,还得长见识。江老回忆,自己小时候曾跟着舅公去过一家纸马作坊。那里的纸马,都是雕版套色印刷出来的。那次经历让他对套印有了直观的认识。再比如那时文学山房的店面和住宅之间,有一个天幔,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客人在此看书选书,江澄波也常有机会学习到他们是如何判断书价值高低、真伪优劣的。更不用说跟同行前辈“交手”,去客人家中送书,这些都是拓宽眼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但从事古旧书行业,光懂得这些知识远远不够,江老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他对自己第一次独立收书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江澄波才十三四岁,清明节去扫墓路过一个旧货摊,见有3本古书,便翻开细看。根据掌握的知识,他认为应是明朝人手写的蓝格抄本,便毫不犹豫买下来。回家后,祖父一番翻看,确定这是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不由对他大为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再比如外出访书、收书,藏家常常只拿出一两本,请他说说书的情况。“这其实是一种考校。能说出‘干货’,说得对,藏家才愿意继续往下交流;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那就难有后续了,人家知道你不识货啊!”江澄波说。访书、收书的实践,便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最佳方式了。江澄波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慢慢成长为古旧书业的专家。
保护古籍,投身中华文化传承
2001年重开书店,是为了减轻家人的生活负担。如今经济上早已不存在问题,但江澄波还是坚守着这间小小的文学山房,想要把书店继续开下去。“保护古书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江澄波说。
江老从业80多年,见过太多古书的命运流转,也深深为那些因为没有落到对的人手中而遭到毁坏的古书感到惋惜、无奈。有一次,江老在一户人家见到一部宋版《后汉书》,但可惜纸张已全部黏在了一起,成了一叠“书饼”。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物主将此书埋在地下,没有妥善密封。他还曾去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的后人家收过书,那时这家已经败落,藏书无人打理。江澄波去时,很多古书外面看起来函套是好好的,但一打开,里面全是空的,书页都被白蚁吃掉了,只剩下一张皮。这令江澄波万分痛心。而战争年代流落海外的中华古籍、被不识货的人当作废品处理掉的古籍,更是不知凡几,让爱书人光是想想就心痛不已。
正因此,从事古籍保护与传承,成为江澄波一生的选择。他年轻时就认为,古旧书从业者最大的使命就是把合适的书送到合适的人手中。胡玉缙、陈奂、管礼耕、费善庆、沈秉成、丁士涵、叶昌炽、王同愈、冯煦等众多名家的藏书流出时,文学山房都曾积极访求,将书送到下一任藏家或机构手中。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传承中,江澄波见证了一部又一部古书的命运沉浮,也了解到郑振铎、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在战乱年代是怎样历尽艰辛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存的。他深刻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对私人藏书家来说,想要世代相传、守护古书,实在是难上加难,毕竟‘累世藏书能几家’啊。”江老说,“公藏机构是古书最好的归宿。”新中国成立后,江澄波有意识地将古书提供给公立收藏机构,经他手入藏各大公藏机构的古书难以确数,其中尤以10部宋版书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东莱吕太史文集》,这部书原是物主寄放在一家鱼竿店售卖的,店主与江澄波相识,遂主动邀请他掌眼。江澄波一看之下,发现竟是罕见宋本,立刻议价收回,后入藏苏州博物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则是江澄波在新华书店旧书回收部工作时,一位上海藏书家主动带到苏州出售的,经江澄波鉴定,旧书回收部收购后提供给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容斋随笔》的流转更是颇为传奇,其中的曲折只有江澄波这些当事人才清楚。
江澄波为古籍保护事业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积极参与促成了过云楼3/4藏书归公,入藏南京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乖崖张公语录》《字苑类编》《龙川略志》3部宋版书。正如江老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书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命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古书能拥有更好的命运。
江澄波的另外一项工作,是为古籍保护事业培养人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的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曾两次邀请江澄波前往北京授课。他认真对待,自撰讲义,还自制实物书《文学山房明刻集锦》,讲授课程“怎样鉴别古籍版本”。这两次培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学员后来多数成为各地古旧书店的骨干,或进入拍卖行业,成为古籍保护事业的中坚。从自己保护古书,到培养他人保护古书,都是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江澄波的这份情怀和业绩,使他成为人们心中德高望重的书林前辈。
如今,97岁高龄的江老,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讲起往事如在目前。他每天上午9时到店,下午4时半下班,坐在自己的“专座”上,看门外人来人往、四季变换,喂一喂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与四方读者和访客聊一聊书林轶事。这是一份坚守,更是一份传承。
(作者单位:古吴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