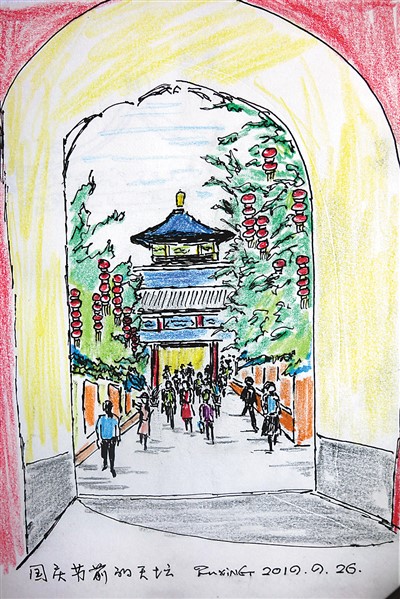一
我常到天坛公园遛弯儿,能见到很多背着大炮一样各式镜头的专业单反相机的人,而且是日见其多。如今,单反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不少老人也玩起了单反,不是尼康就是佳能,尼康D850全画幅,都不在话下。尽管赶不上颐和园冬至那天那么多老人抱着单反拍十七孔桥夕阳金光穿洞、不顾寒风凛冽、拥挤一起争先恐后的那么热闹,但在天坛公园里也常能看到抱着、背着、端着单反拍这拍那的老人。尤其是花开时节,老头儿的长镜头单反,和老太太的花围巾,成为了标准配置,是天坛公园里的一景。
那天,在丹陛桥西侧林荫道的座椅上,一位坐在我身旁的老爷子,指着一位背着单反刚走过去的老爷子,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都是孩子不玩了,淘汰下来给的。
这话说得有点儿酸葡萄味儿,那位老爷子的相机的长镜头,很是有点儿威武呢。我便说:现在有的老爷子不缺钱,自己买得起,也玩得转这玩意儿。
老爷子鼻子哼了一声,瞥了我一眼,有点儿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给我看。是很多照片,照的都是街头小景。我仔细一张张看:新世界商厦门口新开张小店排长队的人群;花市街口等红灯骑摩托车的外卖小哥;磁器口豆汁店门外摆地摊卖鞋垫的老太太;尹三豆汁店门口提着一塑料桶豆汁正迈步出门的老爷子;王老头炒货店里争先恐后买栗子的好多伸开的手臂;光明小学校门前的路上接孩子放学回家挤成一团的小汽车;广渠门桥头摆在地上一堆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色彩鲜艳的蔬菜水果;红桥商场后面卸货的货车旁蹲在地上正在抽烟的司机;夜灯下雪花飘落中不知等候何人正在焦急打手机的男子;细雨飘飞中的斑马线上打着一把红伞颤悠悠过马路的老太太;公交车上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搂着姑娘的情侣;地铁站甬道里抱着吉他卖唱的小伙子;一个手高举着气球正在奔跑的小男孩;几个围在一起吹起漫天彩色泡泡的小孩子;一个已经滩成一滩泥只剩下一双石头块做成黑眼睛的雪人;一个遗落在地上颜色还很鲜亮的天蓝色口罩;一长队隔着两米距离等着做核酸的人们;一群人围观一个正画祈年殿油画的姑娘……
老爷子望着我,虽然没说话,却在眼巴巴地求点赞呢。我连声说道:真不错!真不错!都是您用这手机照的?老爷子说:当然,怎么样,比那些玩单反的照得一点儿也不差吧?
我夸他:比他们强!您这照得多接地气呀,市井人生百态,比照颐和园的金光穿洞,照北海公园里的戏水鸳鸯,或者圆明园那湖里鱼吃荷花,要强多了!
老爷子谦虚地说: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讲究的是技术,咱们讲究的是生活,两路活儿!
说完,老爷子意犹未尽,从我手里接过他的手机,接着又说:玩技术的,得用单反;照生活的,用手机就够了。
我笑着说:手机让您玩得够溜!看您照了多少啊!
这只是一点点儿,好多片子都存在家里的电脑里了。我没事爱到街上瞎转,随手照,人家叫做“扫街”,不讲究什么光圈呀景深什么的,也不修图,就是原生态。
这样最好!原生态比描眉打鬓好!您的这些照片连在一起,就是北京今天街头的清明上河图呢!
您过奖了!您大概也看出来了,我照的这些片子,都在附近这一带的一亩三分地。我家就住花市,远处我也不去。这一带,就够我照的,每天出门,都有的照,照不完地照。
您这是一口井深挖,不仅让它出水,还得出油!
我们俩跟说对口相声一样,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二
和其他公园相比,天坛公园春天的玉兰、杏花、丁香、西府海棠一落,只有靠古树提气。这确实是其他任何一座公园都无法匹敌的。这样的古树,天坛如今一共有3562株。如果不是天坛建坛600年漫长时光中人为的战火与天然灾害的纷乱侵蚀,古树的数目,应该比这个数字更多。
天坛公园里最为人瞩目的古树,当属长廊北侧的柏抱槐和回音壁外的九龙柏了。那里的古树,因为太有名,都被铁栏杆围着,人们无法与之亲密接触。对于我,最喜欢的是西柴禾栏门外的3棵古柏。这么多年,几乎每一次到天坛,都会到这3棵古柏前看看,好像它们是我的风雨故人。
在天坛公园,柴禾栏门有两座,分列祈年殿围墙根儿的东西两侧,当初,是为给神厨宰杀烹饪牛羊等祭品提供烧柴用的。这两座门,如今都是天坛公园的办公之地,西柴禾栏门里放着清洁卫生的三轮车,不对外开放,因此,这里的游人几近于无。门前,3棵古柏,由东到西排列,冬夏春秋,枝叶茂密,郁郁苍苍,如3个威武的壮士,屹立在那里,脚下是草坪如茵,背后是红墙似血,有一股难言而雄浑的沧桑感。特别是夏天,草的嫩绿,树的苍绿,墙的火红,瓦的黛绿,色彩对比得强烈而鲜明,我一直以为,最能代表天坛的色调。这3棵粗壮的古柏,树龄都很老了,一棵560年以上,两棵620年以上。在整个天坛,找到这样年头悠久三位一体并排站在一起的古树,很难了。
那天中午,我从南过花甲门,沿着一溜儿红墙贴身前行,走到墙尽头的拐角处,就可以看见这3棵古树了。忽然,一眼看见,最里面的那棵古柏前,站着一位姑娘。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始终抬头望着树冠。我站在那里,也一动不动,我不想打扰她。很少见到有游人到这里来,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静静地站那里,抬头看树。
我看见姑娘动了,围着这株古柏缓缓地转了一圈,她的手臂不时抚摸着树皮皴裂的苍老树干。那样子,像孩子环绕着老人的膝下,老树因此而变得慈祥,对她诉说着悠悠往事。有风轻轻吹来,枝叶簌簌拂动。中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温煦地洒在她的脸上、身上。因为她在走动,阳光不时跳跃,一会儿顺光、一会儿逆光地在脸上和身上,像蝴蝶翻飞。
我忽然有些感动,为这个姑娘,也为这古树。姑娘对古树如此敬畏。古树值得姑娘如此敬畏。
只是,如今,我们不少人似乎没有或者说缺少这样对树敬畏的感觉。我们一般愿意膜拜神像,却不知树尤其古树,其实也是神,是自然之神。我们应该敬畏大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在有五六百年树龄的古树面前,人也是渺小的。
想起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想跪拜在神的面前忏悔,他没有去到教堂的十字架前,而是跪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也想起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伟大诗篇《变形记》中所写的菲德勒和包喀斯那一对老夫妇,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变成别的什么,只要变成守护神殿的两棵树,一棵橡树,一棵椴树。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树是那样地让人敬畏。在如今,树只是一种观赏品,而不再是一种自然之神。
我看见姑娘在这株古柏前绕了一圈,又走到第二棵,一直在这3棵古柏前全部默默地绕了一圈。
我和她擦肩而过,我很想叫住她,问问她为什么对这3棵古树如此感兴趣,又如此神情充满敬畏?可是,我忍了忍,没有打搅她,像不想打搅一个美好的梦。我望着她走远。
我看清了,姑娘也就二十出头,姣好的面容,马尾辫,一身运动装,白色的运动裤,红色的运动绒上衣,头戴着白色的棒球帽,身背着棕色的双肩包,和苍绿如同深深湖水的那3棵古柏,和那红墙,和那绿草坪,颜色纷繁,像是盛开的一朵奇异的七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