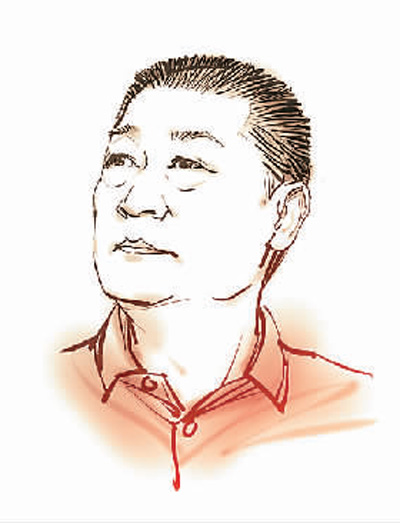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2019年暑假回故乡,照例要到大别山转转。但这次不一样,又往大山深处走了一程。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汤汇镇的一个山坳里,看到一所老式建筑,土墙黛瓦,“六区一乡列宁小学校”的牌匾虽历经风霜,上面的字迹仍依稀可辨。这是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列宁小学。走进大门,认真打量那些铺满时光印痕的砖瓦和无语的门窗,侧耳细听,仿佛听到琅琅读书声,从遥远的天穹、从几十年前的山谷、从洒满阳光的枝叶上泉水般涌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下山的路上,我有点神情恍惚。朋友跟我讲,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也在这座山上,距离列宁小学只有20多公里。我心中一动,预感可能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当时还很朦胧。问了朋友才知道,列宁小学始于1930年,希望小学始于1990年,中间跨度正好是60年。
那时,我正踌躇满志地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暂名《飘呀飘起来》。众所周知,大别山是一座革命山、英雄山,作为一个“正面强攻”军旅题材的作家,大别山已经成为我创作生命的摇篮,成为我英雄书写用之不竭的源泉。萌芽中的《飘呀飘起来》,自然还是以革命战争和英雄塑造为主题。
始料未及的是,这次参观列宁小学,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从山上下来,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鄂豫皖最早的列宁小学,同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同在一个山坳里,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巧合还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然?列宁小学和希望小学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我认为当然有,而且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血脉相连。有理想才有希望,如果说列宁小学寄托着前辈革命者对未来的理想,那么希望小学就是这理想浇灌的花朵。理想、希望,这两个词,就像两只扇动的翅膀,在下山的路上,一直在我的眼前飞舞。
还是那天,晚上在金寨县古碑镇一个黑猪养殖基地用餐,文友相聚,其乐融融,几杯家酿的米酒下肚,全都原形毕露,谈文说艺,高谈阔论,兴之所至,还吟诗作赋。大家起哄要我献诗,脑子一热,潜意识中对创作的渴望和坚定流露出来,一段顺口溜脱口而出,其中有一句是“写不成书我是猪”。这句玩笑话当然也没什么风险,因为我本来就属猪,万一写不成书,猪就猪吧。
现在回想,就是那晚,那件预感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列宁小学和希望小学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灵感,那座一直耸立在我思维世界中的大别山,不仅是一座革命山、英雄山,它还是一座文化山、教育山,也是一座理想之山、希望之山。
从故乡回来后,我决定暂缓《飘呀飘起来》的构思,从根本处出发,首先写写这两所学校,写写这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写写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些人们。为什么又是大别山?为什么大别山人民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中一再承担、牺牲、奉献?因为文化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希望的力量。此后两年,我又重新捧起被我翻阅过几十遍的《皖西革命史(1919-1949)》《金寨红军史》等资料,一张洋溢着红色理想的《鄂豫皖苏维埃建设规划图》被我放大了挂在书房墙上,沈泽民、蒋光慈、许继慎、林月琴等大别山地区早期革命者的形象一直活跃在我眼前,他们被我塑造成了作品中的红军崇山支队司令员韦思源和教官李桐、叶晨霞、胡桃等人物,在他们引导下,一群山里的穷孩子捧起了书本,唱起了《列宁小学校歌》《读书歌》《童子团歌》。
在新的构思里,我写了拉倒(韩子路)、秋子(乔咏秋)、白儿扎、姚菊等少年红军的故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克服贫困,拥有读书的条件并健康成长,有几个重要前提,一是因为他们有幸参加了革命,遇上了韦思源等有知识、有理想、有远见的革命者。即便是在反“围剿”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韦思源也坚持让他们避开血腥的战斗场面。韦思源有一句很温暖的话:“就算崇山支队全部牺牲了,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崇山支队打光了,还可以重建,而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孩子们长大了,可以建设中国。”这番话不仅是红军官兵的理想,也是我本人的理想。第二个前提是,李桐、黄奎、张树等红军官兵身先士卒的牺牲精神,极大地感染了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很早就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树立了崇高的理想,知道应该为谁学习、为谁战斗。三是孩子们的自我教育,帮助他们发育出健全的人格。在由戏班子集体整编的红军宣传队里,拉倒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孤儿、白儿扎是旧戏班子的学徒、秋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下工作者的后代,这些孩子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小小年纪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较之我此前创作的军事题材作品,《琴声飞过旷野》拥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在两年多的准备时间里,我翻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到红军初创时期,许多领导人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有留学经历。基层官兵中,也有不少人读过私塾和公立学校,特别是后来有了列宁小学、速成小学、随营学校等教育机构,更是为部队提供了文化保障。每当我打开电脑注视屏幕的时候,往往就会看见大别山一隅,层峦叠翠的山谷里,明媚阳光下孩子们矫健的身影。他们既学军事,也学艺术;既学社会知识,也学自然科学;既学传统文化,也接受外来文化。基于对历史的认知,我在设计作品框架时,心中始终保有文化的底色,并弥漫在字里行间——学唱《国际歌》、讲世界革命故事、朱玛丽老师传授艺术常识、秋子讲解数理化基础知识……凡此种种,让孩子们的视野掠过大别山,掠过正在搏杀的战场,看到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方,看到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景象……
在飘荡着浪漫气息的文化氛围里,小红军战士们茁壮成长——拉倒成为红军宣传队员后,以一颗淳朴的心灵领悟艺术真谛,以超常的勤奋弥补了天资不足,成为宣传队里的一名琴手,并在对敌斗争中以音符传递紧急密码情报,用艺术为大别山抗战贡献了一份特殊力量。乔咏秋是作品中的“理科男”,热衷于发明,他的理想是抗战胜利后回到大别山造水库,并在战争间隙积累了很多水文资料。在最后一场战斗中,他以艺术的敏感,破译了拉倒用琴声传输的情报,保证了部队里应外合。白儿扎在乔咏秋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最早进入战斗部队,成为一名少年指挥员,并在战争结束后以大别山水利师师长的身份,为水利专家乔咏秋铺路搭桥,在举世瞩目的淠史杭水利工程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把这部作品命名为《琴声飞过旷野》。完工之后的某一天,我坐在自家阳台上,“眺望”两千里外的大别山,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
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红军女战士精神矍铄,娓娓道来——
孩子们,你们总是问我,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啊,后来的故事可多了,后来我们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解放军几万人马,开到大别山,组建水利师。我们宣传队也解散了,多数人都在水利师担负管理和技术工作,我们回到了月亮湾,回到了燕子河,找到了当年帮我们渡过难关的王竹大叔和秋叶大姐,找到了当年失散的战友……我们和几十万大别山人民一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土洋结合,艰苦奋战,终于,我们建成了……建成了……孩子们,你们看啊,那里——
老红军伸手一指,群山之间,白云之下,巍峨的佛子岭水库大坝横空出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