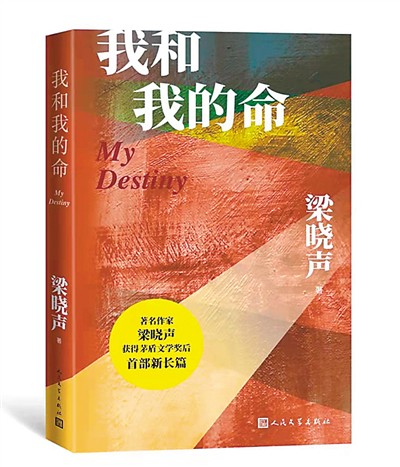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谈一下《我和我的命》的创作初衷。
作家的职业可以从多方面诠释,但有一点肯定是不会错的,即——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给更多的人也就是读者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长文《扫描中国女性》,文中对某些困难家庭中的长女表达了敬意,认为她们是那些家庭中的“责任天使”。
后来我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说她的“小五姨”就是那样的“天使”。信中有段文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小五姨”是姐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毕业);是家族中最早离开山里农村到深圳打工的人;于是呢,“小五姨”在深圳所租的那间小屋,仿佛成了家乡设在深圳的“办事处”。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龄,外甥、外甥女们以及同村甚至外村的小青年,纷纷投奔到“办事处”来,多时连地上都横七竖八睡着人。“小五姨”早上像跳芭蕾舞似的在身体之间回旋,寻找鞋子。她从无怨言,尽量为每一个投奔到自己名下的小青年排忧解难。可“小五姨”只不过辈分大,年龄并不大,才25岁……
那封信使我很感动,我附上自己的感言,把它转给了一家杂志发表了;似乎当年的《读者》也转载了。
原来“责任天使”未必是一个家庭的长姐!
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小五姨”,从此存活在我的脑海中了。有时会忘记她,有时会联想到她,彻底忘记已成不可能之事。每一次联想到她,从她的样貌、性格到她的心灵和人生观,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再联想到时,仿佛她在对我说:“还不把我写出来吗?”
我越来越觉得,她是值得我“写出来”的。
她的“出生”非常顺利。因为动笔时,头脑中的她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之大多数“80后”是独生子女,“90后”“00后”及以后若干代可能也是如此。出生政策虽已放开“二胎”了,但多数家长恐怕宁愿选择做独生子女的父母。
独生子女由于是一个家庭的“独苗”,也必然会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心目中的“宝贝疙瘩”,这使他(她)们想不以自我为中心,都不知怎么才算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几乎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本我意识”。
故而,以我这一代人的眼光来看“80后”,不免“毛病”多多。
如今,年龄最小的“80后”30多岁了,年龄最大的40多岁了,而我从他(她)们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首先有一点使我十分佩服,那就是——我们成长于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而他们的成长背景物质诱惑多多,有时形成诱惑的泡沫堆,从四面八方包围,撕扯成长期的少年和初入社会的青年,大有淹没之势。第二点是,我们就业后经历了较长的“收入普调”和“住房分配”时期,这使全中国同龄的脑体力劳动者,在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看来,那种差别几可忽略无视。而我们的下一代,在尚未就业之前,就已受到收入差别天上地下般的现实的巨大压力。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80后”,总体上非但没有自暴自弃,没成为“垮掉的一代”,没成为社会的“零余者”,反而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不消说,他们大多是平凡的,但“拒绝平庸”显然是他们的“代精神”。努力点儿、再努力点儿,优秀点儿、再优秀点儿,也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共识。
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我这一代人集体回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他们所终日面对的诱惑和财富分配差异的巨大刺激,我们果真能表现得比他们更好吗?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也常起一种大的冲动,想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探究他们的真情实感,叩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一向是被采访者,没有机会采访年轻人。即使有那样的机会,也未必能获得如实的回答。
于是我又联想到了“小五姨”——她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一个”,就经历而言,与后来的年轻人有一致性,也有独属于她自己的特殊性。
然而就那种不甘自暴自弃、不甘“垮掉”、不甘成为“零余者”的内在精神来说,我认为我笔下的主人公们,与当下大多数青年或许会是“知音”。而在这一点上,我笔下人物的性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笔下的方婉之和李娟们,会成为当下青年们的朋友吗?
毫无疑问,“她们”已成为我的“忘年交”,我因有这样的朋友而愉快。
我活到今天,由文学作品而结识的朋友也已不少,有些是别的作家介绍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我“塑造”了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比他(她)们高出一等;恰恰相反,他(她)们往往也对我为人处世的态度产生了深刻而良好的影响,成为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至于方婉之们,她们肯定也会有她们的“社会关系之和”。“她”在人世间境遇怎样,我也只能深情关注……
(作者系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