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的小说,一半是煤,一半是土,他多年的创作一直都没离开这两个方面。纵观他最近的作品,《黄泥地》关注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态;而《黑白男女》叙述的是矿难之后,矿工家属如何继续生活的话题;这次的长篇小说《家长》依然没有离开煤矿和乡土,却又不太典型:一方面,小说主人公延续了矿工家属的人物谱系,另一方面也包含乡下人进城的话题,在原有故事架构基础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体现了题材上的求新求变。
《家长》开头的节奏比较舒缓,不急于进入故事,描绘出一派恬静自然的乡村生活场景。然而在闲谈中,又抖落出一段逸闻:六年级某女孩被爹娘训斥之后赌气自杀。在不经意间为整个故事埋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笔。不错,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正是《家长》的重心所在。整个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部写给“家长”的“警世恒言”。
毫无疑问,用文学的方式处理这类社会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乡村和煤矿的故事与现实太过切近,固然可以引起有关家庭教育等社会学议题的讨论,但似乎很难从中提炼出可以生发的精神性命题。刘庆邦在小说序言里戏称自己是在“念难念的经”,对于评论者来说,小说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难念的经”?
今天的纯文学作家普遍不愿涉足公众话题,大概会觉得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做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小说流于通俗而不愿屈就;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欠缺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样看来,《家长》对于当下创作的启示显而易见。“新闻结束的地方,小说如何开始”的老生常谈在刘庆邦这里有了新内涵。
《家长》中,王国慧一家大概算是典型的中国家庭,父亲忙于工作,对孩子的事完全不操心,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对孩子施加诸多负面影响。母亲王国慧对孩子要求太多,管得太多,管得太细,管得太死。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儿子,这大概是所有家庭悲剧的根源。而为了儿子则体现在对孩子学习的片面关心上,孩子的学习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必须为孩子的学习让路,所有的悲剧也因此而来。错误的家庭教育会毁掉一个幸福家庭,而《家长》显然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
整个《家长》的叙述语调包含着一种微妙的反讽,小说并不指望读者依据移情机制顺利地站在主人公王国慧一边,相反,作者有意要让人们看到她的自以为是,从而塑造一个负面的母亲形象——“中国式家长”的典型。应该说,王国慧这样的家长构成了今天中国家长的绝大多数,他们自己辛苦奋斗大半辈子,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孩子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导致儿子何新成精神失常。这显然是当代文学中一个令人警醒的母亲形象。因此,《家长》试图引出的话题在于,我们今天怎样做家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家长变得越来越焦虑,围绕学区房、课外班和升学考试挖空心思、寝食难安。《家长》犹如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也让我们不断检讨自己,王国慧会不会就是我?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成为何新成?小说揭示出某些家长狭隘的成功观:有钱有地位才是成功,快乐不是成功。所以在家庭教育中,不少父母不愿意让孩子甘愿去做一个平凡人。因此,《家长》的警示意义在于,如果所有家长都在不断“奔忙”,所有的孩子都在被迫“上进”时,何新成的悲剧就在所难免。
对于《家长》来说,乡下人进城也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叙事线索。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母亲王国慧显然适应得不错,尽管她刚开始甚至不知道开家长会要不要坐在操场上,但她很快就能得心应手地按照城市逻辑行事。但对于未成年的儿子来说,这种转变很难被迅速适应。纵观何新成人生轨迹的突变,从农村到城市是不可忽视的一环。何新成一下子失掉了在乡村小学时的优越感,他在班级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雷打不动的三好学生变成学校里被嘲笑、被欺负的对象,这不可避免使他的心里装满了委屈。而作为家长,王国慧不仅没有及时疏导孩子的情绪,反而以各种形式加重它,最终让孩子走上歧路。小说在这里设置的进城情节,将单纯的教育问题勾连起复杂的城市化进程,为所探讨的家庭教育问题平添了现实的厚重。
《家长》也写到一些别有意味的细节。比如,作为三好学生的何新成有一次旷课跑到赵老虎家,帮卧病在床的赵老虎倒尿壶,结果被王国慧狠狠教训了一顿。这里当然有赵老虎忽悠未成年人、让他为自己服务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让我们看到何新成内心的善良。结合此后的花猫事件,以及与周丽娟的恋情,小说偶尔会透露出一种微妙的叙事声音,呈现孩子的赤子之心和纯真天性。恰恰是这些隐而不发的部分,能够让人感受到整体讽刺氛围中溢出的情感涟漪。
“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林斤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刘庆邦的小说。以平淡朴实的方式,关注寻常人生,进而提炼出平凡却深切的启示,这是刘庆邦的贡献,而他的《家长》,再次让我们领略了这种可贵的品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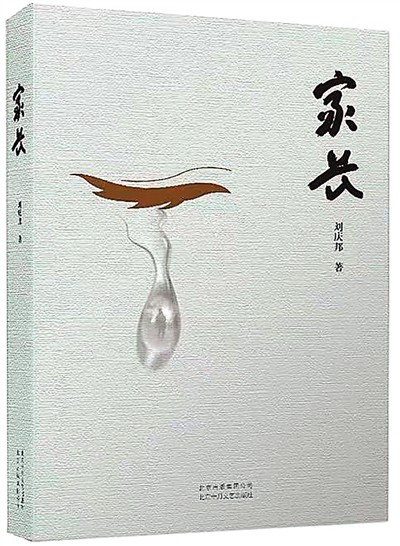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