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生活》是我和批评家张莉对谈文学的书。跟张莉聊文学很开心,因为张莉有很好的知识储备,最关键的是张莉真的很懂文学、懂小说。批评家不做虚构性工作,所以每当谈起文学时都是从一套体系出发,时代、美学背景、文化风格、人性、民族,从这些话题出发去映照小说。批评家真正用手指摸到小说的人不多。而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其实不懂文学,我们就知道写,我们感受到一些东西,用种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人们把它命名为小说。通过一篇小说呈现怎样的历史、呈现怎样的时代,这不是作者想的事情,是他这个小说呈现的过程中,很可能跟这些话题合上了。
所以批评家和作家,理论上是很好的聊天伙伴,其实是过不到一起去的“两口子”,一个是川菜,一个是淮扬菜,如果两个人相敬如宾,你吃吧,你吃吧,过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但生活在一块不一定行。张莉是可以跟我吃到一块的批评家,从我俩“过日子”的方式里面能感觉到,我也是一个可以和她吃到一块去的小说家,所以我们在一起聊就很容易。
张莉在出发之前,大的思路捋得特别清楚,我甚至都不用考虑吃完午饭聊什么,她开一个头,聊三四个小时,等到吃晚饭我们就吃晚饭,晚饭之后进入哪一个话题,我就顺着她走就行了,特别简单。我聊得很简单并不意味着我对这本书没有要求,我内心是有要求的。我这本书给读者之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和张莉一起完成的。从我这边来讲,我要让读者看到的是具体的那个叫毕飞宇的人,他的文学、他的小说。
虽然我们两个都不是学哲学出身,聊哲学可能更有意思,那些大概念,你刺激我、我刺激你,谈完以后两人都很嗨,那些问题有很好的批评家、学者、教授去做,它们是学问,是历史。我坚信读者从我这要得到的应该是非常具体的文学话题,甚至可以说是跟具体的个人生命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文学,或者个体生命在小说里的具体体验,我们两个彼此挖掘、激发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本书是小的。一个好作家让读者最后发现的是这个人的生命,他的内心,这才是一个作家最牛的事情。否则人家去看哲学、看历史,看一个作家的诉说干什么呢?你要有能力把你的胸膛打开,通过一个特殊的光学装置,你必须把自己提供出去。所以我所有的愿望就是小,就是具体,具体到把这么大一个包装盒子打开,里面有一个小盒子,再打开,里面又有一个小盒子,再打开,里面有一个塑料的小袋子,最后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光学装置,因为他有很好的信誉,他的读者透过这个光学装置知道他不骗人,这才是成果。
虽然我现在是南京大学教授,但我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踏踏实实地把一个作家该说的话说好。而不是因为做了教授,出于虚荣我必须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教授,以教授的身份去说话。多亏了这本书,我避免了我的虚荣,我收获了我的诚实。我避免了一本糟糕的书,我收获了一本不完美但是特别像我的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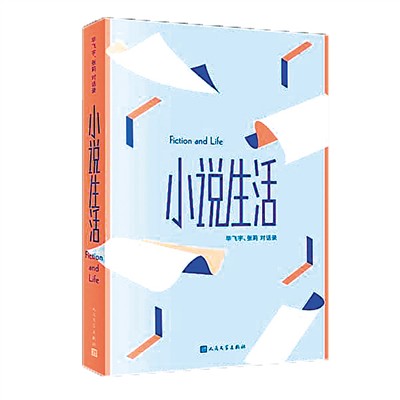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