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孩子们知道什么,想了解点什么?”
不久前,成都大学教授胡珍举行了一场以“谈性说爱”为主题的讲座。地点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听众都是高二年级的学生。
孩子们兴致很高,胡珍让大家用纸条写下自己想听的内容。打开一看,胡珍有点意外。
“我统计了一下,70%学生都在问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统称)、‘嗑炮’和‘文爱’(通过语音或文字聊天来满足自身性需求)、‘耽美文学’……这些内容无一例外都是从互联网上看来的。”胡珍说。
在近日于河南省林州市举行的全国学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交流会上,胡珍以此为例,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抛出了问题——“我们知道青少年在关心什么吗?我们怎样从青少年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需求?”
性骚扰、性侵害、艾滋病低龄化……近年来,多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让性教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尽管如此,什么是“性”、如何开口谈“性”等话题依旧是社会的敏感点。性教育的开展与普及,也常常成为围绕在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间的一场“无声博弈”。
面对阻力与不解,仍有人负重前行。交流会期间,来自性教育领域的专家与教师,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与困惑。
是堵,还是疏?
大三学生小光,受大学同学邀请一起出去玩,在一家会所中和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的同性朋友吃饭、唱歌。在朋友的诱惑下,小光尝试了性兴奋药物,并与朋友发生了性关系。等到过后因发烧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在交流会上,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王克荣讲述了诸多自己亲身经历的病例。“很多孩子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直到得了艾滋病才感到‘一切都完了’。”王克荣说,艾滋病感染的低龄化令人心忧,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少年缺乏防艾等性健康教育。
事实上,如今的孩子并不缺少性知识的获取途径。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让“性”内容几乎触手可及。“父母和老师要认识到,你不教性知识,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不接触、不思考。”胡珍说。
但性教育的进行,绝非“百度一下”就能解决。
“真正的性知识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互联网上的信息良莠难辨,充斥着大量诱惑性、挑逗性内容。孩子很可能从中受到错误的引导,认为这就是性,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胡珍说。
遗憾的是,面对海量信息的冲击。不少家长和老师的选择是“堵”——恐慌和禁止,而非“疏”——交流和教育。正如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所言,我国青少年性教育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是学生对性知识了解程度与性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国家政策高度重视和家庭与学校教育缺位之间的矛盾。
囿于文化和观念等因素,家长和老师不了解性、羞于谈性,是我国性教育普及步履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对性健康教育有顾虑,实际上是对性教育的意义和内涵不够了解。性教育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乃至一生的健康和幸福都至关重要。
胡珍形容,自己每次给老师和家长做培训和讲座,都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告诉大家性是什么。它不只是性交、性行为。”
“有些家长觉得,艾滋病离我的孩子远得很,对这些性教育听都不爱听。结果呢?孩子就像小光一样,受到了伤害。”胡珍说,“性教育的目的并非解决艾滋、性侵等单一问题,而是为了让孩子有能力保护自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作出负责任的选择,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幸福的人。”
很多性知识更丰富的“80后”“90后”为人父母,为性教育的开展扫除了障碍。但胡珍表示,面对互联网等海量信息的挑战,很多家长和老师仍然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作为教育者和父母,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我们自己应该有高于孩子的性知识和态度,并有教育方法上的积累。”
孩子太需要这些知识了
“妈妈怀孕真辛苦啊。”在课堂上,学生们轮流在胸前挎上书包,模拟妈妈怀孕时的样子。看到肚子里的“宝宝”让自己“卧立难安”,几名小学二年级的男孩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性教育课该怎么上?在交流会期间举行的青爱工程种子师资教学成果展示会中,13名中小学教师针对我从哪里来、预防校园欺凌、认识艾滋病、正确处理异性交往关系等课程举行了课堂展示和交流活动。
“《小霸王与受气包》《月经与卫生巾》《青春的秘密花园》……谈及这些不同主题的性教育课,青爱工程办公室主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别有一番感触。
“我们把性教育叫做‘幸福一生的教育’,不同的年龄段要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如果到了高中和大学再去补课就太晚了。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就应该知道,自己的隐私部位别人是不能触碰的,如果这样的知识早点儿给到孩子,本可以避免很多儿童性侵害案件。”
张银俊介绍,于2006年启动的青爱工程(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以“青爱小屋”作为推手,已在全国1073所学校开展了防艾和性健康教育,累计培训师资9000余人次,受益学生、教师和家长达1340万余人次,初步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青少年年龄特点的学校性教育模式。
而所谓的“种子教师”,则是青爱工程从2015年开始的“种子师资培训计划”,针对青爱小屋的教师,进行为期4年、每年两次、每次7天的性健康教育专业培训,旨在建立起全国性的性健康师资培训平台和后备团队。
培训老师,先从“脱敏”开始。参加培训的老师,有不少原来并非专业心理健康老师。别说讲课,就连开口也成问题。
河南省林州市桂园学校语文教师李艳,因为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懵懵懂懂”地被校长“拽”去了种子教师培训。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性教育是讲什么的。在北京听专家讲课,我觉得每个字眼都很敏感,心里也有点排斥。”李艳说。
可没过几天,李艳就脱敏了。“我越听越发现,孩子太需要这些知识了,而我们之前的教学忽视掉了这一块。”
对此,张银俊感同身受。“很多老师都是这样的情况,都是被‘逼’上讲台的。可一旦老师跟学生互动了、开了口,都会非常热爱性教育,真心愿意去做这件事。”
开了口,还得开了课。针对不同孩子的阶段特点,专家和老师设置了一系列课程。例如小学一年级的“孵蛋宝宝”,用保护鸡蛋的方式感受母亲怀胎的不易;二年级了解“我从哪里来”;三四年级了解如何预防性侵;五六年级则开始学习男女的不同性征和艾滋病预防。
“对于这些课程,孩子们没有任何排斥。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不像我们成人一样头脑里有那么多画面。”李艳说,“老师讲课也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让孩子自己体验和感受。”
四川省都江堰市顶新新建小学教师杜丽也认为,青少年的性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
“现在很多青少年的初次性行为提前了。如果我们的性教育及时跟上,孩子就会知道做这些事情会有什么后果,知道自己要承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越做心里边儿越敞亮
接受了性教育的孩子,变化显而易见。很多孩子发现,原来性这件事,是可以和老师沟通交流的。
“体育课遇上生理期,女孩子会明明白白地告诉老师,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还有的女生主动跟老师借卫生巾,这在以前都是没有出现过的。”李艳说。
云南省盈江县第一小学教师张改说,性教育课的开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贡献良多。
“在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刚满18岁甚至未成年的孩子,互相看对了眼,寨子里放一通炮仗,男孩就把女孩给‘拐’过来结婚了。上了性教育课,很多女孩认识到,不能过早地同男性有性接触。目前我们地区的怀孕低龄化趋势已经有了好转。”张改说。
杜丽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一位女老师有个5岁的儿子。以前每次都是爸爸给孩子洗澡,有一天爸爸出差了,妈妈打算帮孩子洗。没想到儿子抗议了:‘妈妈你给我洗澡,不要看我的隐私部位’。”
在很多学校,性教育课都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性教育老师也变成了校园里的明星。“在校园里碰到学生,很多孩子都问我,‘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上课呀?’当全校3000多名学生都能毫不费力地认出你时,你不会感到自豪吗!”李艳说。
改变的不止孩子,还有家长。
除了面向青少年的性教育课程,青爱工程还开设了“家长课堂”。张银俊说,每年青爱针对家长的课程就有五六百场。“做性教育,如果家长不认可则很难推进。所以我们要给家长扫盲,讲清楚性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家长同意了,这门课才能开下去。”
“到现在,为青爱工程捐款的人中,大部分是学生家长——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性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张银俊说。
李艳说,现在每个学期自己都会在每个年级开一次家长课堂。除此之外,一些学生课堂也面向家长开放,让家长打消疑虑。
“通过家长课堂,所有的家长都同意我们开设性教育课。很多家长说,性教育课帮他们说出了不好意思对孩子谈的话题。很多孩子上完课后,还会主动同家长沟通——‘原来我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真不容易’。”李艳说。
在青爱小屋的经验分享交流中,杜丽的一席话感动了在场的老师。
“做了10年青爱,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人。2008年汶川地震,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一共有60个孩子,只剩下了4个。这10年间,我学会了怎样更好地和父母、丈夫、孩子相处,学会了怎样去爱他们。”杜丽说,“做性教育,越做心里边儿越敞亮。”
“这些默默无闻的一线老师,因为性教育课成为了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成了全地区最美的老师,让他们得到了人生出彩的机会。让学生、家长、老师从中受益,正是这样的动力,驱使着我坚持把青爱工程做下去。”张银俊说。
用心耕耘这些种子
在谈及自己的教学经历时,很多老师都提到了来自学校的支持——在林州,当地政府投入1500万元为青爱工程提供资金保障;在盈江,青爱小屋的种子老师遍布全县,很多缅甸同行也前来交流经验;在都江堰,校长的支持让杜丽从语文教师转岗成为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
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有这样的幸运。张银俊说,很多青爱小屋的老师得不到学校的认可,上课不算课时费、没有奖金。“陕西宝鸡的一位老师,上了几百堂性教育课,跟校领导磨了半天,最后折算成两节课的课时。但就是两节课,也让他很高兴,至少自己的工作被认可了。”
性教育课程、性教育老师得不到认可,是张银俊最难过的。“青爱工程刚启动时,我们带着资金和专家到学校,一所一所地谈,平均100所学校里有一两所愿意接纳就不错了。”
很多专家和老师表示,对于性健康教育,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卫生部门都已有相关规定,将防艾等性健康教育纳入教育规划之中,对于课程的开设也有明确要求。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监督规范,导致课程的落实情况难以令人满意。
“我在各所学校介绍经验时,很多学校负责人和老师都来加我微信,希望我把性教育课程带过去。既然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性教育就不该成为某些学校的‘特色’,而是应当成为一门真正的课程。”李艳说。
国家很支持、学生有需求、教师有热情。尽管如此,青爱小屋在各地的建设,仍常常要面对前功尽弃的风险。
“明明知道这个人快渴死了,需要喝水,我想给他送一杯水,但是却给不到。”张银俊打比方说,很多血淋淋的案例让她感受到,尽早接受性教育,就可能避免艾滋病和性侵害等伤害。
为此,张银俊逐步改变了青爱小屋的进入“策略”——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同学校进行合作。目前,青爱工程涵盖了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公益慈善、传统文化等五方面的教育内容,学校可以从中选择一项或几项建立平台,随后再逐步引入其他方面的教育。
例如在林州,青爱小屋最初是以公益慈善教育的角度来推进的;而在都江堰,则是借助灾后心理援助和疏导,逐渐为性教育的普及打开了心理的窗户。除此之外,青爱工程还将在今年年底推出视频课程,以期解决师资短缺和培养成本过高等问题。
很多专家和老师也期待着,希望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加强师范院校在这方面的师资培养。
“现在我们通过青爱工程培养的性教育老师都是在职教师。如果能够在师范院校加入通识课或辅修专业,那么未来老师的工作会顺畅不少,孩子也能从中受益很多。”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说。
“社会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变成一种国家行为,才能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我希望有一天,性教育能够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在全部学校中开展。”张银俊说。
“10年前,我们这些性教育老师是种子。其实,我们的孩子、家人,我们的家庭、千万个家庭都是种子。只要我们用心去耕耘这些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 杜丽说。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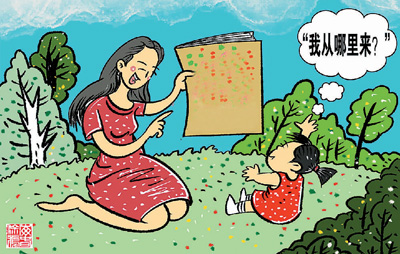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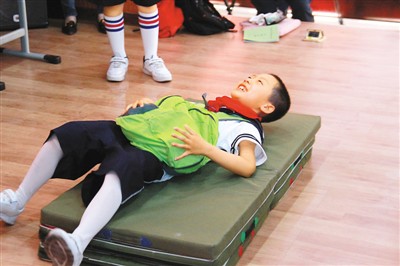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