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创作以治水名响天下的李冰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我钻进了故纸堆,走在了河流两岸。还因少小的桤木记忆和中国诗篇中的桤木情怀,我从未停止过对桤木的追逐。三条不同的行进线路,在成都西边,一条以桤木命名的河流上,不期而遇。
以桤木为名的河
这一天,我游历到桤木河湿地一带,春雨潇潇,蜀雾清淡,看不见鸟儿的身影,只听见鸟儿的叫声。2014年始建的桤木河湿地公园,大大提振了这条河流的美誉。否则,恐怕这条归于岷江三级支流谱系的人工河,依然是籍籍无名的。遗憾的是,桤木河湿地公园里的桤木,似显稀薄了一些,拜访桤木,必须绕开众多名木的遮蔽。
说到桤木河的得名,应该是“桤木河以河边多桤木树,故名。”这再自然不过。《大清一统志》曰:“岷江分而南流之溪木河即此,盖不知为桤字,以崇境此木独饶,故水受斯名矣。”这部清朝官修地理总志说得更细,既说了这河得名,又说了这河先前为溪木河,后才正名为桤木河,之所以错谬,乃是因为不知世上有个桤字,更以为桤木树为崇州特产。这显然是编撰者对蜀地植物知识的欠缺与寡闻,当然更可能是不懂装懂的臆度。
我在六岁前,在四川灌县,就见过和知道桤木树了。“玉垒以东多桤木,易成而可薪,美阴而不害。”(《蜀中记》)玉垒即指灌县岷江边李冰凿离堆的玉垒山。显然,我降生的地方,是一个桤木成林的所在,而李冰当年拦水筑堰所用杩槎中的木料,亦采自本地盛产的桤木、柳树和杂木。
六岁时,我随家迁居到大巴山腹地万源县。在万源,我家居的地方都临水,最先是后河西岸的盖家坪,后来是后山坡下的水库边,再后来,是后河东岸的二重岩,也就是我母亲至今居住的地方。生长在盖家坪和水库边的日子,约等于被桤木庇护的日子,我家屋前屋后,全都站满了身披铠甲的中老年桤木。翻开《秦岭巴山天然药物志》就知道,“桤木枝梢”还可入药哩,嫩叶亦可作茶饮。想起饕餮自己亲手采回的桤木菌的样子,至今都满嘴生津。春天,青翠的桤木用树叶边缘的象形木锯和嘴唇,向天空表达着自己的情愫。秋天,无风也瑟瑟飘零的落叶,像一场提前到来的无边大雪,向大地报答着自己的感恩。四季更迭,树状叶色随之而动,让人常看常新,百看不厌。
桤木的品格
徜徉在桤木河两岸长长的绿道上,我还恍惚看见了一些文化人简册基底里的古蜀木纹——桤木的木纹。最出名的当然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堂成》。老杜的桤木诗本就有名,偏又来了个苏东坡的《杜甫桤木诗卷帖》,其书法艺术的高境,以及一写再写的桤木诗篇,更是把桤木世界的文格和心灵秘史推到了极致。此外,扬雄、王安石、陆游、李劼人、朱自清、叶圣陶、汪曾祺等,都曾与桤木有过文化交集。
桤木的种子漂再远,都是沿着河流去的。桤木的血脉流再遥,根都在古蜀。稍稍作个田野考察就会发现,四川,以桤木为地名的地方,不计其数,为天下之冠。成都地区,有崇州桤泉、龙泉驿桤木沟、双流桤木塘、简阳桤木村等。成都以外,有屏山桤木湾、峨边桤木坪、高县桤木林、沐川桤木坝、荣县桤木冲、荣经桤木溪、甘洛桤木顶、万源桤木树梁,以及乐山五通桥桤木沱、沙湾桤木槽等。可以断定,但凡以桤木为地名的所在,无一例外林立桤木,无一例外临水而居。这一点,你一句不问,桤树的别名就告诉你了:水青冈、水漆树、青木树、萝卜柴、旱冬瓜树、水冬瓜树……
还可以断定,在文化的向径上,桤木河的性格、功能,就是桤木的性格、功能。“朱崇堰在公议乡将军桥以上为桤木河上流,灌溉农田一万八千多亩,将军桥以下有民堰三十七道,灌溉农田十万余亩。”《朱崇堰上迁堰口碑记》以精准的数据昭示,桤木河可以滋地肥田,继而出粮,继而养民。而这,恰是桤木之实用性的对标翻版。
跟桤木河一样,桤树也能滋地肥田。《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单狐之山多机木”。机同桤,即桤树。郭璞注:“机木似榆,可烧以粪稻田。”这个说的是把桤木做柴薪烧成灰后,用柴灰肥田。桤木树有个最大的特点,特别适宜人工栽培,且三年即可长大成材。桤木虽系硬木树种,但其材质一般,重量中等,抗压强度、消震性、韧劲和抗腐蚀能力较低,因此,多用作柴薪和寻常人家的家具木器。从这一点看,桤木树居于树木王国底层,是树木中最普通的树种——它真像是树木中割了又长、长得疯快的草啊。桤木树的寿命较短,只有二十余年。但它的繁殖却是方便的、迅猛的,花籽呼拉拉掉落地上,它就呼拉拉长了起来。桤木木质均匀,纹理清晰,颜色多样,手感细腻,制作成型方便。正因为这些特点,又因其外貌与山毛榉相仿,一些重利而狡黠的商家便用桤木冒充“缅榉”。而一旦被揭穿,遂辩称听错了,自己不辨桤木榉木的发音。
桤木之根在古蜀
明末清初广安人欧阳睿年在他的《蜀警录》中讲了自己经资中入简阳地界时,遇四虎、过河溪、遭暴雨,险些淹死,终被“桤树岸”救命的故事。而江西《崇义何氏九合谱》中则讲了一个桤树帮一家人度过灾年且有娃崽生出的故事。
公馆如林的大邑县安仁镇的饮用及灌田用水,主要取之桤木河。就是说,刘湘、刘文渊、刘文昭、刘文成、刘文彩、刘文辉等人无不是喝桤木河的水长大的。但桤木河的水则是有限的,一到旱季,上游崇州人就关小甚至完全关闭朱崇河堰口的闸门,这无疑断了下游安仁等地沿河一带人的血。于是下游人号聚上奔,砸闸挖堰,强力放水。械斗和血拼开始了。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周而复始,随天行事。两县县官一直在协商解决,又一直不能解决,这让多少县官如坐针毡,丢了官帽。但更着急更受难的还是饥肠辘辘的百姓。直到民国二十年冬,由包括时任省主席刘文辉在内的刘家人物亲自出面主持,才在上游味江河凿口,另开新渠,引一脉山水入桤木河,彻底解决了此事。
最有意思的是,以桤木命名河流的,四川仅成都地区就有三条。除了崇州的故事纷纭、传奇古今、乡村味十足的桤木河,还有郫都的用渠骨撑开的桤木河,以及源出龙泉山文安场,经青白江、金堂后,汇入沱江的行不改名坐不更姓、野性到底的桤木河。
对于桤木的原生地,古蜀文明专家、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向以鲜教授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桤木的原生地就是蜀中,所以桤木又叫蜀木。而且这个‘桤’字,我认为是古蜀语的遗存。古蜀语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汉语分支,融合了古羌语、古彝语等多种文化元素。秦灭巴蜀之后,古蜀语受到致命破坏,但仍有一些词语化石幸存了下来,‘桤’正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一句话,桤木,蜀木也。
(成都凸凹,又名凸凹,本名魏平。诗人、小说家、编剧,著有《甑子场》《大三线》《花儿与手枪》《蚯蚓之舞》等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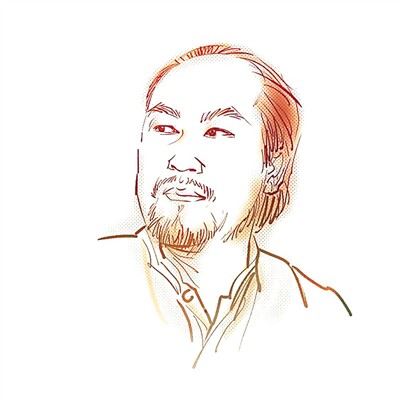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