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园学习、生活了二三十年,自以为对这里的事事物物已相当熟悉。然而,展读何晋教授的新作《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却意外“发现”了北大校园一些习焉不察的故物与故事。
何晋兄不愧是历史学者,他数十年实地观察和细致钩沉既有材料之所得,让我在校园里重新走了一个又一个来回。既加深了我对燕园风物的了解,也让我对这个校园的精神意义有了更多思考。
说起来也许有几分反讽意味,与现在许多追求“西化”或美其名曰“现代化”的校园建筑大相径庭,这个由“洋人”墨菲设计的校园,至少外观上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的设计灵感得之于“西边远远可见的玉泉山塔”。这位“在那个时代提出中国古典建筑复兴理念的人物”,根据燕园的地形,设计了一条东西主轴线和一条南北副轴线。“两条轴线有主有次、阴阳和谐,东西轴线均从建筑物之中穿过,南北次轴线则均从建筑物之间穿过。校园内以这两条轴线为中心的众多建筑,大多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形式,风格上典雅而又统一”。
如果说,墨菲的上述努力,还只是体现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将中华文明与现代知识有机结合起来的理念;那么,整个校园中心建筑——办公楼(施德楼)的设计,则格外发人深省。
这所建于1926年东西朝向的两层大楼堪称巍峨。她正面朝西,背山面水,十分宏伟。在何晋看来,它比“紫禁城的任何一个殿堂都要高大”,而且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整栋楼建在一个须弥高台之上,而建在高台之上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等级高的重要表现”,恰如故宫的三大殿;其次,这座建筑与绝大多数中国古典建筑或许不同,她“东西南北四面(都)有门,从门前台阶的形制上看,后门和两侧门为‘垂带踏跺’”,即台阶两边有垂带石,中间为踏步。而正门(西门)的台阶则采用了台阶的最高形式——一般用于宫殿正门之前的“御路踏跺”,“其标志是台阶中有一块台阶石,又称‘陛石’‘丹陛石’”。
如果不是何著中如此细致的观察与分析,我们大概完全不会注意到建筑师在巧妙使用中国古典建筑形式时,所进行的有意或无意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内在而具革命性的。至少在一个现代建筑师的主观意识中,知识的或真理的殿堂本来就大于并高于皇权的与政治的殿堂?而通向真理之门的才是神圣的“丹陛”,并且,真正的真理殿堂之门也应该朝向四方洞开?
对此,我们当然无须求之过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施德楼的设计和建设者在试图接通古典中国传统的同时,显然并没有完全遵循既有的限制和规定性。何晋兄观察到,施德楼的主体并没有采用最高规格的庑殿式建筑方式,而恰恰采用了次级别的歇山式,采用庑殿式的反而是两翼的耳楼。这种对既有秩序和规矩的“肆意”改变或扬弃,这种主与次之间的移位,墨菲和同伴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吗?更重要的是,多少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燕园走过,我们意识到了吗?
当我们充满感情地像胡适之先生那样赞叹这所“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园子的建筑形式及其精神构成,与传统中国的内在联系究竟是什么?飞檐、斗拱、麒麟、石碑、石舫、品字形院落……乃至基督教教会学校里完全不合乎规范的“(佛)塔”——博雅塔,这些一望而知的中国元素,代表的仅仅是古老的过去吗?还是,所有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被墨菲,被司徒雷登,更被蔡元培、被李大钊……被中国与外国的先贤,被兼容并包的校格赋予了新的意义?既是古老的符号乃至图腾,又是一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追求真正深层变化的精神象征?走在燕园,我们能不有所反思,有所追怀,甚至有所反省吗?
燕园里还有多少这样我们习焉不察的故物与故事?
就说未名湖吧,这是我们多么熟悉有时却又多么陌生的所在?如今,这美丽的湖泊,已成为北大的标志。但认真阅读何晋的记述,我们一定不会再简单地仅仅将她视为一处景观,或一个凝固的符号吧?
“未名湖的形成,大概可以追溯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叠山造园大家叶洮规划设计‘自怡园’时”。“乾隆时,未名湖周边一带被赐给了宠臣和珅,成为清代著名园林‘淑春园’,和珅又名之‘十笏园’”,“园中水田被开凿为大小连属的湖泊,挖掘起来的泥土堆筑为湖心的小岛和环湖的冈阜,现在的未名湖,即是保留下来的淑春园中最大的一个湖泊”。
而“未名湖”这个名称,似乎也并不如一般所传闻的来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是当时在燕大任教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给出了这个没有名字的名字:一个最具精神性也最具可塑性的命名。
说起来,全体北大人也许都该感谢一位名叫约翰·M·翟伯的化学教授。作为当时校园基建部门的负责人,翟伯教授保留了未名湖不规则的形状。如果按照规划者墨菲原先的设想,为了严整的空间秩序和对称性,这片美丽的水域,不是被无情填埋,就是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沟渠。试想,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将是一个怎样“规矩”、无趣而失去创造力的北大?
这两件彼此呼应的故事,也许在无声地告诉我们燕园的某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象和品质。也许就精神存在的意义而言,作为知识与真理的圣地,燕园本来就应该是无形而又有形,有序而又不羁的吧?
读毕何晋兄的新作,我想问他这个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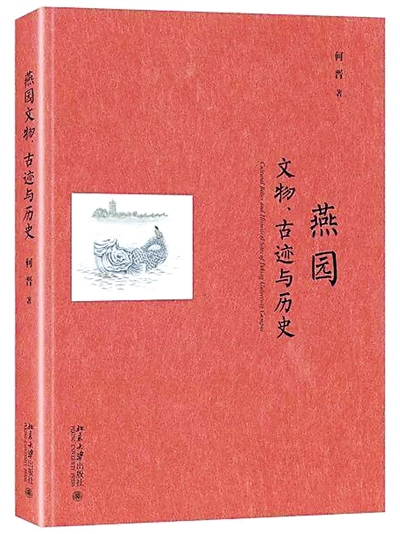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