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还会想起那些书信,还会翻翻它们,从中找寻旧岁月的痕迹,当然,某些记忆也会被它们唤醒。从我记事起,我们已经搬过多次的家,从某地到某地,再从某地到某地——但那些书信却没有丢失,它们被略显郑重地摆在书架上,犹如一排站立笔直的列兵——我知道“列兵”的比喻已经不够新鲜,可我看到它们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却依然是列兵,是方阵,也许这与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有关,与我同样是一名军人有关。每次搬家,我们都会丢弃一些舍不得的旧物,几次下来旧有的东西越来越少,只有这些书信被完整地保存着,跟随着我们。那里有父亲母亲的青春,也有我成长中的岁月。它们,俨然是我们家最珍贵、最不能舍弃的旧物了。
父亲是军人。那时我还小不知道“军人”的含义,只是感觉他总是不在,总之,他是一个让我想念却又模糊着的高大影子,他一回来,我就腻在他的身侧变成他的尾巴,我想好好地记住他,可随着时间他又一次次变得模糊,成为一个身影。至少梦见的时候是这样,在梦里他往往只是一身绿军装,可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是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想念了,邻居家的姐姐、弟弟们应当也是,虽然我们都没用过想念这样的词。
父亲不在的日子,写信,等信,几乎是母亲闲暇下来的全部。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母亲每周去父亲老部队的收发室取信的情景,在那份依稀里,母亲是有光的,她的发梢上、身体里散发着我也能察觉的光亮。她抱着我,她觉得我走得不够快,似乎走得快了父亲的信也就能到得快一些,里面的信纸也会厚一些……受我母亲的影响,每周五下午于我也像是一个节日,一个挂念和让人期盼的节日,一个让人跟着紧张起来的节日……那时候山里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快递,有的,就是信函。母亲抱累了,放下我,我会跟着她奔跑,就像奔向一个必须要紧紧追赶才能得到的,礼物。
父亲总是繁忙,他不能每周的周五都让我母亲收到他的信,当然有时母亲会一次收到两封……母亲奔向收发室。她让我去敲门。然后,她的速度慢下来,仿佛随意,在一大摞信件中随手地翻着:老张家的,小李家的,赵哥的——前天嫂子还抱怨呢,这不,信就来了。月月,看你齐叔叔的字,写得多好,比你爸爸的字还漂亮……我抬头望着她,而她的眼睛只盯在信函上。她那么认认真真,不肯放过信笺上的每一个字。
有时,没有父亲的信。没有父亲的信的时候,母亲往往会从头至尾再翻一遍,直到再次确定,没有,父亲没有信来,他的信经历了某种我们想不到的阻隔,它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或许还磨破了鞋子。“没有信,”母亲会说一声,至今我也不确定她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自己。“走吧,我们回家。”这句话是说给我的,她会伸出手来,拉紧我的手。回去的路,我们便不会再那样匆忙。
偶尔,母亲会把父亲的信念给我听,尤其是提到我的部分。每次听到父亲在信里提到“月月”或“我们的小月月”,我都会激动不已,我觉得父亲信中的文字真是美妙,有力量,有气息,有那么浓那么浓的情感……后来,我翻翻他们之间的信件,竟然有种失落在——他们的信其实平淡如水,在我童年时感觉的美妙、力量和那么浓那么浓的情感竟然没有了痕迹。在谈及我的时候他们的确话显得多了些,但也只是平常的询问和平常的叙述。他们说的,在信中说的都是日常,家里遇到了什么,今天谁谁谁家遇到了什么,我在野外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还有什么……我发现,我的父亲母亲都不习惯“形容词”,当然更不习惯的是抒情。在信件中,他们的表述是那么地平平淡淡,最多是,“天凉好个秋”,注意加件衣服。那些美妙,力量,气息,和那么浓厚着的情感都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它,是母亲在读信时候才注入的?那她为什么在那时候要注入这些?
还是,它们其实在着,掩藏在了纸的背后和字的背后,掩藏在那些平平淡淡的背后,那些叙说的日常是虚掩的门,他们会在读信的时候将门推开,里面,有一个空阔的、情绪的波涛一直汹涌的天地?
在书架上的家书方阵中,夹有一封我的信,那是我的第一封信,它,写给我的父亲也写给我的母亲。信的内容是:爸爸妈妈,我怕黑,你们不要我了吗?
就是这些字,只有标点是后加上去的。多年之后,当我在翻看父母保存的家书的时候忽然地翻出了它来,它,竟然也被精心地放在了书桌上,是他们的宝贝。爸爸妈妈,我怕黑,你们不要我了吗?看到自己歪歪扭扭的几个字,我差一点让自己笑出声来,随后则是,突然地泪涌。我记得,当然记得,很可能会永远都记得。
那一年,我4岁。
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反正,院子里升起了大朵大朵的烟花。应当是一个节日吧?我记不得那个具体的日子,但记得后来的发生。我,是在父亲的营区大院里被急急赶来的一位叔叔抱走的,我不认识他但认得他身上的军装。“我们去哪儿?”叔叔小跑着,“卫生所。”
我们赶到卫生所的时候母亲已在那里,她,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愣愣地塞着两根透明的管儿,管子的另一头则连接着氧气瓶,我知道它——“我妈妈,她怎么啦?”我小声的向旁边的叔叔询问,他没有回答。
鼻孔里的两根透明的管子,让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母亲,一个让我甚至恐惧的母亲,不说话不睁眼的母亲。我,都不敢叫她,不敢凑到她的身边去。
一辆绿色的大卡车停在卫生所的门外,这是父亲连队唯一一辆运送物资的车,它,成为了母亲的“救命车”。母亲被匆匆忙忙的叔叔们连床抬到了车上,然后消失在黑暗和崎岖的山路上。“今年,煤烟熏着的可真多呦,”搂着我的王大婶小声地啧着嘴说,她是我的邻居,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是她和付阿姨一起发现我母亲煤气中毒的,她们,也想叫我母亲去看烟花。
那天晚上和接下来的十余天的晚上,我都被“寄存在”付阿姨的家里,她和我妈妈一样也是军嫂,那个时代,大约是因为经历相同的缘故,我母亲和这些“军嫂”们的关系可亲近了,就像一家人的感觉,当然家家户户都是如此,一直是相互照应。
没有妈妈去收发室取信,付阿姨便承担起了她的“任务”,她拉着我,抱着我,她似乎不像我母亲那样着急。和我母亲相像的是,她也会一封一封地认认真真地翻看,然后,又重新再翻一遍。“阿姨,有我的信么?我爸爸来信了么?他们提到小月月了么?”我昂着脸,向付阿姨询问。
没有。付阿姨也许不忍心说这句话,她飞快地抱起我来:走,月月,我们去买好吃的!
那天晚上,我在付阿姨的帮助下,写了人生的第一封信。那些字,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太难了。写着,写着,我就哭了起来,眼泪就浸在了纸片上。我写下的就是那句话:爸爸妈妈,我怕黑,你们不要我了吗?
这封信,连同我留在纸上的泪渍,真的寄到了我父亲的手上。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时间变迁和地域的变迁,父亲母亲,竟然把它始终留了下来,将它放在了我们的家书列阵中。那天晚上,我写完这封艰难的、而又泪水涟涟的信,便安然地在付阿姨的怀中睡去。之后,在我父母回来之前的所有日子,她都始终睡在我的身侧,讲着好听的故事哄我,开上半夜的灯。
母亲跟着父亲,从南方到北方,从大山到城市,那些有见证的家书也一路跟随,它们在慢慢变厚,直到有了智能手机,有了电脑里的聊天工具。可那些家书还在着,始终地在着。偶尔,我竟然怀念他们那个写信、读信的旧岁月,怀念那个时光里的美与简陋,生动与呆板,包括悄悄含在里面的黑暗和疼痛。偶尔,我还会突发奇想,假装自己能够回到那个旧岁月里去,假装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QQ也没有微信,有的,只有必须一笔一划写下的纸。这样,我就会给我的父亲母亲再写封信——是的,我真的写过这样的一封信。
那时,我从省城进入到山里,那种摇晃和颠簸让我以为自己真的重回了旧岁月。我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军队,我不知道牵引我的是什么,就是知道我也不会轻易地说出那个词,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家书里只有家常,只有叙述,而有意压制住字词的温度。他和她,甚至从来没用过想、爱、思念这类的词,他在谈论自己的繁忙和努力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用过责任或者崇高之类的词,他们不用,但不能说没有。我来到山里,听风声雨声,听雪落下的平静与呼啸,听院子里的哨音,有时竟然恍惚地以为,我,其实就是那个离开我们三四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的父亲,我在“体验”他的生活和他的经历,更重要的是,我在“体验”他面对远方和自己的寂静时刻的心境,那里面,可能有和可以有的纤细。有时,我从一个忙碌中走向另一个忙碌,从营房的一个点快速地走向另一个点,我会觉得,我的脚步其实踩在了父亲的脚印上。在那个时刻,我和他融在了一起,和他的岁月也融在了一起。
“一九八四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的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父亲写的散文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个傍晚,那一刻,我突然地那么想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想念简直像一座雪崩着的山。我哭泣起来,然后不顾同事诧异的眼神忽忽跑回到宿舍里面。那天晚上,我给我的父亲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写到最后。我忽然觉得我刚刚的情绪已经化解,它在淡下去,淡下去——我不太应该让它来影响我的父母,让他们担心,嗯,其实我挺好的,没什么,没事,都会过去的。我将刚刚写好的信叠好,放在一边,然后又重新写了一封平静平淡的信,寄给他们。
我没有收到父母的回信,收到的是母亲打来的电话。这其实挺好,在电话这端,我当然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小月月,这里面没有半点儿的伪装。我只是向她承认,妈,我挺想你们的。就是想。在她准备挂断电话的前一分钟,我对她说,妈,我现在知道,你和我父亲的信件里,有什么了。
说完,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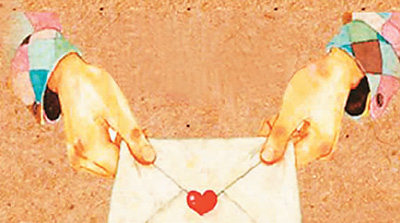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