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首先介绍晨槿。她是曾晓文作品《重瓣女人花》中的主人公。这部中篇小说因为描写不孕女性的题材而引人注目。不孕女性是一个精神上的弱势群体,晨槿受到婆母从中国到加拿大持续不断的冷暴力,她也在这种冷暴力中心甘情愿地毁灭自我,丧失了人格尊严和基本生存条件,进入了人生的黑暗期。
不幸的晨槿遇见了幸运。西人律师凯琳自愿为她辩护,让她看似无望的案件峰回路转。然而出狱后的晨槿依然陷入自卑、麻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同为不孕女性的凯琳成立了“重瓣女人花”俱乐部,在这里,个人命运开始具有了社会意义。晨槿开始走出狭窄的自闭,走入了广阔的人生。晨槿终于在友情、爱情的温暖和大自然的启迪中找回了生命的自洽和尊严。人性的自救和救赎,成为了作品最后的结局。
在曾晓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自救和救赎这一主题的反复出现。在她笔下,很多人物都经历过激烈的人生波折,入狱判刑等重大人生事件在不同小说中的反复出现,并不是作家对故事情节奇巧的盲目追求,相反,它们是个性化人生经历在作品中的分裂、交融和体现。
社会案件往往是人类情感聚焦的爆发,而在爆发之后的种种人性是作者致力挖掘的线索,沿着这个线索层层递进的写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人物命运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由此揭示出人性的层面,这是曾晓文写作的特点。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中,社会新闻是相对隐性的,它体现在肖恩这个人物的命运中;在《重瓣女人花》中,这条线索是显性的,开篇就是家暴,然后逐渐递进,层层深入。但无论隐性还是显性,都是作者写作的切入点,是对人性挖掘的独特视角。
在人物命运的悲剧之后,曾晓文写作的重点往往是生命修复的过程。小男孩展飞之于蓝鸟队的诺瑞斯(《小小蓝鸟》),凯琳之于晨槿,肖恩之于蕾,疗伤是相互的,也是永恒的。在小说《特洛伊木马记·2015》中的薇琪,在修复电脑病毒时也要修复自己。曾晓文曾经说过,她写作的过程是缓慢的自我修复的过程。
修复是有指向的,修复需要自救和救赎。在曾晓文笔下的人物都具有自救的勇气和能力,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苦难中拯救自己。蓝鸟诺瑞斯通过帮助病孩展飞实现梦想的过程,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而蕾,在与肖恩若有若无的情感交流中,通过一个并不完美的爱情,获得了实现人生意义的机缘。他们都因为来自不同方面的爱而得到了救赎。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永恒的命题,比如给予,奉献,爱与悲悯。也就是说,在曾晓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都指向相同的主旨,这就是爱的救赎。
爱的救赎的写作是曾晓文写作明显的特点。曾晓文作品中有明确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是绝望彷徨,不是迷茫压抑,而是自我在艰难境遇中的奋斗和生命的回归。而在曾晓文写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普遍的命题,即海外华文的写作者,其文化发生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他们写作的开端往往印证了文学发生中最本质的缘由,就是“不平则鸣”。而这种“不平则鸣”,因为对自身境遇的倾诉和对身边他者生存状态的叙述,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更加值得关注。
治愈的主题,一直是曾晓文作品中的精神线索。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重瓣女人花》这两篇小说中亦有深刻体现。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治愈。晨槿与蕾都是这样被爱治疗的人,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通过自爱和爱人得到内心的平复和提升。蕾在经历了肖恩的死亡之后,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两个人一段爱情的结局,由此升华到对其他人的关注和帮助,是作品达到的另一个高度。爱最终战胜了孤独和死亡。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平等地讲述中西故事,是曾晓文提出的文学观点,而她的创作是对这一观点的具象表达。在《重瓣女人花》中,这种平等的视野表现得更加明确。在小说中,她不仅讲述了华人女性的故事和命运,还讲述了西人女性的故事和命运,更讲述了她们之间的真挚友情,这种信任和互助建立在平等的人格之上。尽管依然保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在对待命运的安排上,却达到了共识。晨槿在凯琳的启发下,开始正视内心并改变着对不孕女性命运的看法,她逐渐找到了自信。在这里,人物的性格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狭窄冷酷的家庭走出来,走向女人俱乐部,走向纽芬兰,这是走向独立自尊的过程,也是一种走向多民族相互理解和交流的过程。可贵的是,作者的叙述是平静和平等的,在作者笔下,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文化,都包含着某种共通的意蕴。
蕾的爱而不得,晨槿的爱而复得,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而苦难终成财富。这种人生升华的主题,在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这正是她们经历苦难之后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的达成,无所谓种族和国籍,无所谓肤色和语言,只关乎相同的人性。在相同人性的探索与融合中,讲述人类共同的故事,这是海外作家的特点,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我曾经生存过,我曾经奋斗过,我曾经抗争过”——而不断抵达人生崭新的风景,这就是曾晓文作品中自救与救赎的含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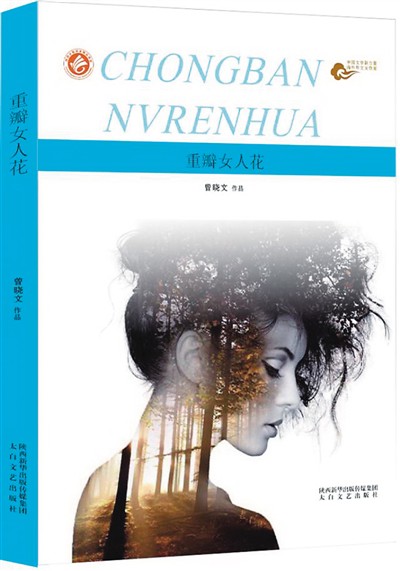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