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来美已有20余年。由于我在华人社区和国际学院的工作,常常接触到许多在美多年或是初来这里的华人。大家在用中文交流时总是倍感亲切,说到兴起还会冒出两句地道的家乡话,免不了常有一出认亲大会,原来是老乡啊!去年年底起,我决定参选美国威斯康星州第三大学区同时也是全州学区中成绩排名第一的Elmbrook的学区董事,也因为这个事,体验了一把“搞政治”的感觉。华人社区是我的助选团,多少次在寒风中与我一起挨家挨户发送传单,提供了许多支持。
无论在宣讲时、还是在私下的交流中,很多朋友总是爱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竞选校董?”我也无数次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争这个在许多人眼里吃力不讨好的事做?思索许久后的答案是,我来美20多年一直孜孜不倦地为社区公益做事的所有热情、激情和责任感,都来源于我童年成长的道路,来源于大洋彼岸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家里有5个孩子,我是老大。上个世纪60年代的山村,贫瘠得只有满山满眼的泥土地。如果说我最先接受到的教育,那一定是来自于我的父母。我的父亲从不奉行“棍棒出孝子”,甚至从未训斥过我。在我的记忆中,他很温和,大家都称呼他“好人”。记得每次去外婆家,田间的小路要走1个多小时。多少次,要过没有桥的河道和泥泞的小道时,他就把我扛在肩膀上。上小学以后,无论他到哪儿,除草种地、煤场扛煤、上山拉石块,他都带着我。我在他肩头看着他走过的路,听着他和乡亲们讲过的话。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印在了我的心底。后来的我变成了他的影子,跟随着他步入成长的路。
上高中后,因为离家太远必须住校。那时候每个人都从家里带一床被子,半边供垫半边供盖。南方没有暖气,刺骨的风就在宿舍里呼呼地来回刮着。到了冬天根本不够抵御四面八方阴冷潮湿的寒气。大家就想了办法:把床铺合并起来,两个人在一起睡,相互取暖。还记得我是和后来成为了诗人的海子睡一个被窝的。总之就那样度过了几个冬天。
高中毕业后,我运气不错考上了北大。从乡下到北大燕园感觉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首先是乡音难改。刚刚入学上英语课,老师让我们每个学生站起来读26个英文字母。结果老师指出,我大部分字母的发音都是错的,为此我发誓要好好练口语。当时想买一个收音机学英语,可是没有钱,只好从每月补助的生活费里省。每顿饭就只买份两分钱的咸菜,说是咸菜其实就是一片腌萝卜。为了不让别的同学看见尴尬,我就把买来的一片咸萝卜往馒头中间一夹,独自从食堂走回宿舍,一路上边走边吃,就这样过了两个月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个19元人民币的收音机。大学毕业后我到中科院读研究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也申请到了中科院青年科学基金。后来还主导成立了青年科学家俱乐部,常请外边的专家来开讲座、进行交流。
在我看来,教育极为重要。尤其是我们那一代人,践行了教育改变命运这一说法。如果没有父亲撑起一家的生活负担,顶着压力没让我辍学回家种地挣工分,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到美国之后,很多亲戚朋友向我咨询各种留学问题。听到乡音的我倍感亲切,也去帮忙。但就在几年前,请我帮忙咨询高中留学的朋友开始慢慢变多,而我发现很多情况已经爱莫能助。于是就开始建立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和大芝加哥国际学院,来帮助小留学生解决低龄留学中遇到的生活、学业、文化融入等问题。很多人无法理解我的选择:这份工作非常繁琐,同时责任重大,艰辛难以道尽。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期,通过我和团队的工作,能够帮助和影响许多孩子和家庭,成就感也非其他工作所能比拟。
这次参加美国Elmbrook学区董事的选举也是这样,本意是想要凭借我已有的一些经验去服务、帮助更多的人,其次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更加了解美国的公立教育体系,以便融入我们东方教育中优秀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
文到这里,我想,我在教育事业上的热情和不计成本的投入都有了合理的解答:是我的父母,我的故乡,我所成长的那个时代和我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共同造就了一个现在的我。在故乡的那些日子,是生活给予我的礼物与财富,让我即使在多年以后,在异国他乡,也依然有着自己的信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不禁想起,刚来美国时,英语还说不纯正。经过这些年在海内外的闯荡,早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随时英语、普通话、家乡话相互转换的本事。而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出来再久,一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讲家乡话,或许是岁数大了,或许是在外面游荡太久,想念家乡了吧。
(寄自美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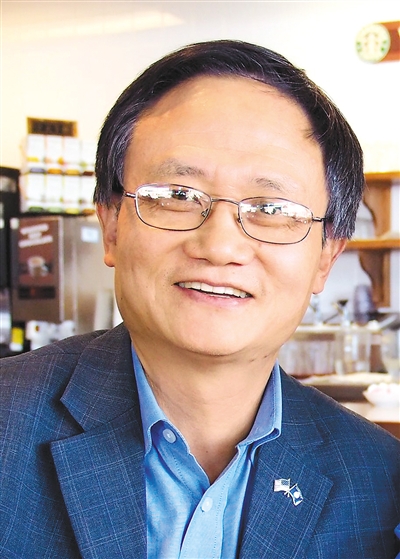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