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上海书展,一直为文学热情张罗的走走匆匆忙忙对我说,晚上弋舟和田耳来,你一起吃饭吧。其时我刚写文学评论不久,还在左支右绌地尝试摸索自己的风格,来不及知道文坛上的秀出人物,正准备问弋舟和田耳是谁,她已经赶着去张罗别的事了。吃饭前准备询问的时候,她却还没等我开口,就已经告诫道——不要劝弋舟喝酒。待我要问一下为什么,并说明自己早已戒除了劝人喝酒的恶习,她却又一阵风似的去忙别的了,我只好带着一肚子疑问先找地方坐下来。
不久,弋舟就来了,单肩斜挂着一个双肩包,迈着一种似乎精心设计过的步伐,面色黯沉,深情落寞,没有跟人热络寒暄的意思,于是也就各自无话。那天饭局有十三四个人,气氛颇为热烈。我因为牢记着走走的嘱咐,跟弋舟只象征性地碰过一次杯,其他时候,就见他在一个人默默地喝酒,等喝到后来的时候,眼睛便开始湿润,唯沉默保持不变。饭局快结束的时候,田耳从别处赶来,随之便掀起一轮高潮。田耳显然已经喝高了,好像在嘟嘟囔囔跟大家道歉,却谁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的时间,我就看着田耳东倒西歪地在座位上摇晃,不时还挣扎着要站起来敬酒和接受敬酒;那个被禁止敬酒的弋舟,仍在自斟自饮,只不时抬起湿润的双眼,茫然而无辜地看着大家。
后来,走走带给我弋舟的《刘晓东》,并跟我说,写得好,语气斩截到不容有丝毫犹疑。不知是不是心理暗示,反正我读《刘晓东》的过程中,耳边就不停地回荡着“写得好,写得好”——确实写得好,因为起码,小说里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作者形象,即便在沉默里,也有种无遮无掩的柔弱,带着明显的幽辟孤冷,跟我那天晚上所见的正同——即使你并不喜欢:“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他失声,他酗酒,他有罪,他从今天起,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首先开始自我的审判。”
后来我就找了弋舟的其他书来读,更觉得能与那天晚上的印象符合。《刘晓东》之前的作品,有一种飘荡的幻想气息。那些小说中的平常日子,有绵延致密的细节和具体而微的想象,尤其是对人物内在情感的处理,揣摩功夫下得透,转折处布置精心,没有常见的突兀和尖锐,准确能时或看出作者深邃的用心。可等这一切团拢起来形成整篇,却又似乎跟所谓的现实并无太大的关系,现实中的干净或污秽、温存或敌意,仿佛都经过了意识的再造,笼罩上了一层明显的反省色彩,磨去了其中的粗粝感,显出整饬的样子。或许是因为这有意识反省牵连的对人世的怜惜,即使再小的事情,再琐碎无聊的瞬间,都能渗透出浓重的悲悯感,显示出独属于弋舟的艺术质地。
《刘晓东》于此更进一步,把反省指向自身,开始了自我审判。上世纪80年代已还,理想消退,琐碎代替了崇高,时代的聚焦点从理想变成世俗,原先光芒四射的人物也颓废在尘世里。在这样的时代交替里,人们最为普遍的心理,就是默认时代的选择,把责任推给时代和他人。最后,是看起来柔弱无力的刘晓东,承担起了反省的责任。他有自己卑下的心思,复杂的爱恨,挣扎于绝望和虚无之间,矛盾重重,犹疑不定。可最终,只有这个柔弱且矛盾重重的自我审判者,才是小说中唯一担当起反省这个时代的人,因为只有他明白,世界的败坏与自己有关。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反省者,检省着自己对眼下这个糟糕世界的责任,不置身事外,不借故推诿,而是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微弱力量,努力打开他经历的时代,见证它的起伏,体会大变动中人的委屈,在小说里洗净荒芜世界留在一代人心里的伤口。
或许是因为《刘晓东》中明显的自罪感,我觉得弋舟此前小说里的悲悯,似乎也转进了一层,流露出某种庄严的气息,堪称书写或一情形的标志性作品——自《刘晓东》之后,所有推卸责任式的书写都将失去价值。只是,我在被鼓舞的同时,却也有了些隐隐的担忧,小说在自省同时流露出的自怜式的柔弱感,很容易把人捆缚在某些细致周密的固定频道——或者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的担忧,柔弱的自省有时会把人从生活的烟尘中生拉出来,耽溺在意识的(故作)清净境界里,就如弋舟自己说的那样,过上一种奇怪的“二手生活”。
2015年暮春,我因机缘待在北京一段时间。有天中午,忽然收到弋舟短信,问我是否在鲁院,他正巧来京,或可一见。仍然是单肩斜挂着一个双肩包,迤迤逦逦走进了鲁院的食堂,相约晚上聚聚。那时张楚还待在滦南过他的“一手生活”,弋舟电话过去,“一手生活”立刻乘大巴紧急赶来。晚饭吃到十一点,弋舟的话多了一些,酒意却仿佛刚刚上来,意犹未尽,于是又赴簋街夜宵。开喝不久,一个抱着吉他的歌者在店外徘徊,弋舟忽然感动起来,从他的双肩包中掏出钱来递出去,却并未点歌,而是自己走到歌者的位置上,满怀深情、满眼泪花地高歌了三曲。据说歌声动人的“一手生活”,就那样看着“二手生活”完成了自己的深夜演出,当然并没有忘记鼓掌。
那天晚上的歌声几乎消除了我的担忧,也让我无端相信,弋舟引用卡尔维诺小说中的那段话,不是借机标榜,更不是心血来潮:“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生活在烟尘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这种雾蒙蒙的空气,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用弋舟自己的话来说:“我终于明确地知道,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背景,就是我一切悲伤与快乐的根源。我想,也许当我竭力以整全的视野来关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时代的破绽,这也许会赋予我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唯有此,才能解决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轻浮,让我以缺席的方式居住在避难的时空里。”
《丙申故事集》的出版,让我确证了自己的感觉。这本集子收入弋舟丙申年写作的5个短篇,让人觉得作者对世界的容含度提高了,小说打开了一个特别的内在空间,新的血肉生长出来。生活的烟尘大面积地在小说里蔓延,却奇崛鲜烈,于人世的萧瑟孤寂处透显出顽韧的生机,从而有了更具活力的庄严,就像那个“地铁菩萨”——“车过高碑店时,上来一个女人。她大概有50多岁,很胖,肚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但她却穿着件正常身材的人穿上都会显得逼仄的小夹克。她浓妆艳抹,面无表情地坐在我的对面,长长的蓝色睫毛一眨不眨。她旁若无人,像一尊正襟危坐着的膨胀的菩萨。我突然感到羞愧难当。这尊地铁里的菩萨猛烈地震撼了我。在我眼里,她有种凛然的勇气和怒放的自我,这让她看起来威风极了。”
我把弋舟的这批小说,称为“盛放在拗格里的世界”。它安置了世界本身的粗砺和不完整,却不是削齐磨平,而后让它再生般地重生在虚构的世界里,就像古诗里的拗格,看起来每一处关键的平仄都不对,却在全诗完成后呈现了全备的美感。除了偶尔还是会流露出的幽辟孤冷,那些亘古长存的山川、劲力弥漫的日常进入小说,打开了人内心的某些隐秘之处,勾勒出早已被现代小说遗忘的雄阔野心,阅读者或将缓缓感受到其中含藏的巨大能量。
前几天,弋舟在朋友圈偶尔晒出了冯象翻译的《摩西五经》和《智慧书》,并略述心得。我不禁猜测,这个一直在小说技艺上不懈向上的人,现在算是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和叙事经典吧,他将会如何借此调整有时轻易示人的柔弱,打开自己略显夸耀的幽辟孤冷,又是怎样把身心所得惬洽地安放进新作品中呢?他或许会充分意识到,时代和自身的破绽,都必须经过更为严苛的反省,因为小说写的,并不是平常生活,而是对平常生活的洞见。有分教——非关幽冷俏模样,庄严赋尽烟尘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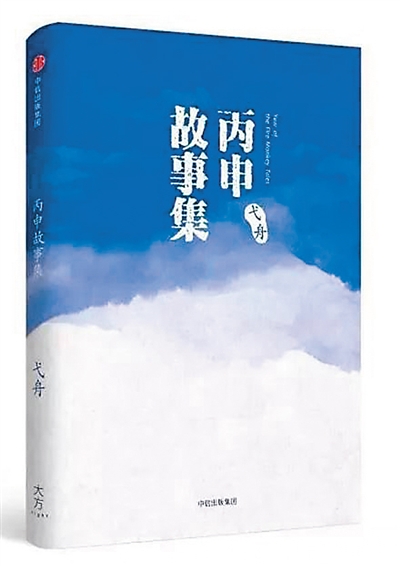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