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的书,须慢读。一手执卷,一手从碟子里拈豆子、瓜籽,咀嚼着,再呷口绿茶,慢慢品咂,各种滋味交互错杂,入口入心,其境妙不可言。
这本《闲话闲说》,讲的是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中国文化的精髓被阿城归结为4个字“世俗精神”。“世”是世间大众,“俗”是约定俗成,说透了,就是人间烟火,百姓恩怨。想那黄土之上,苍天之下,悠悠千载,亘古不移,这烟火卷帙便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朝代更迭,帝王将相如走马灯一般,外来入侵的铁蹄踏碎小村的鸡鸣狗吠,骑青牛的老子描绘乌托邦时,也不过借的是升斗小民的朴素愿望——“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题目大,但篇篇落脚世俗生活,由此生发、阐释,自寻常中析出理论。
他说: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鲁迅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
他说:世俗间颓丧的多是男子,女子少有颓丧。女子在世俗中特别韧,为什么?因为女子有母性。因为要养育,母性极其韧,韧到有侠气,这种侠气亦是妩媚,世俗间第一等的妩媚。我亦是偶有颓丧,就到热闹处去张望女子。
读到此,我心中大乐。这家伙的大朴素之处,恰在于他虽俊逸,却并非不沾荤腥。正如他讲:色不可无情,情亦不可无色。或曰美人不淫是泥美人,英雄不邪乃死英雄。
他还说:圣人就是俗人的典范、样板,可学。英雄是不可学的,是世俗的心中“魔”。
这些说辞,往往掷地有声斩钉截铁,他却当作闲话来闲说,如陌上赏春、花落旁家一般漫不经心。
阿城说到中国的世俗信仰,认为道教管理着中国世俗生活的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所以历来世俗暴动,总以道教为号召,陈胜吴广、黄巾赤眉、汉末张角、清朝义和拳;中国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成仙了,仍要携带世俗,就好像我们看中国人搬进新楼,阳台上满是旧居的实用破烂”。这个比喻,打得人心里一惊一叹。
谈到世俗小说,他几乎将“腔调”视为艺术奸细,提起来,便一顿笔墨老拳。他说“现在有不少‘闲书腔’和‘闲读腔’,搞得人闲也不是,不闲也不是,只好空坐抽烟。”关于“腔调”,阿城的观点可概括为:做什么,但不能有什么。小说不能有“小说腔”,寻根小说不能有“寻根腔”,翻译不能有“翻译腔”。
他评价当代小说,说刘震云的《官场现形记》,是“沙漏一般的小世小俗娓娓道来,机关妙递”,湖南何立伟的小说有诗的自觉,南京叶兆言弓马娴熟,上海的须兰,笔下世俗渐渐滋润,浓妆淡抹开始相宜,北京王朔,火爆得沾邪气。他说王安忆的《逐鹿中街》是世俗的洋葱头,一层层剥,剥到后来,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正在恨处妙处。
阿城自嘲说:你们要是问我的东西有没有腔,有的。
至于什么腔,他没说。依我看,他的《闲话闲说》,有的便是闲话腔,不玄虚,不疏远,举手投足透着随和,叙事论说高妙有味,说古论今,侃文逗艺,透露着浓厚的人生逸趣,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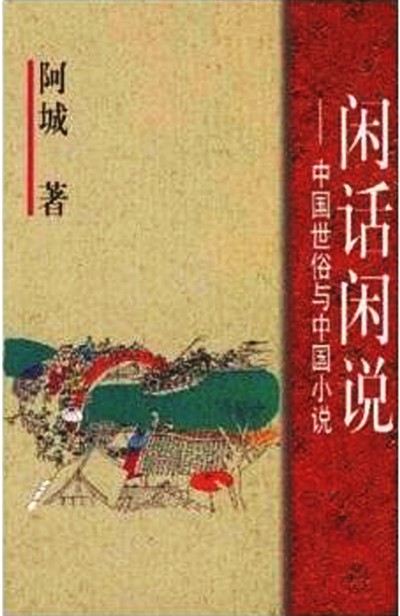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