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80余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几十万人浩浩荡荡的万里长征,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对持续近10年的国共内战,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还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开宗明义地称之为人类英雄主义的一次证明,它的意义比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攻打巴士底狱这一历史事件更有价值。作为红色历史上的辉煌一页,它被诸多的小说家反复书写,绵延不绝,给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文本,也给人们留下了历史与文学的深刻启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富有生活质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描写红军长征的小说,首先来自万里长征的亲历者,作品多以质朴而富有生活质感见长。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根据红军长征中的一件历史文物,写了《金色的鱼钩》。这部短篇小说,以一个患病体弱的小战士的口吻,讲述老炊事班长在粮食匮缺的环境下,将一枚钢针改造成鱼钩,给3名小战士改善伙食,增加体力,使他们得以走过长征,老班长自己却因为长期饥饿而遭致衰亡。故事单纯明快,童心盎然,因此一直保留在小学语文阅读教材中,感染了几代后来人。出生于贵州苗家、在16岁时加入红二方面军的陈靖将军,他的小说《金沙江畔》,描写在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兵败身亡的金沙江畔,红军官兵有勇有谋,通过启蒙和团结少数民族部落,顺利渡过金沙江天险,粉碎了国民党要让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如意算盘。《金沙江畔》问世之后,被改编为同名评剧和电影,广泛流传。陈靖和黎白合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则是表现红军长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也赢得了很多的读者。另一位苗族女红军马忆湘,13岁时加入红军的长征行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出长篇小说《朝阳花》。作品描写了13岁的小红军吴小兰和她的战友们,一群年轻的女性的长征经历。其中吴小兰在掉队之后,不畏艰难寻找和追赶红军部队的情节,感人至深。
红军长征的传奇经历,也吸引了后来的年轻作家,王愿坚就是在采访老红军的故事中获得灵感,写出一批描写红军长征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三人行》《路标》等。这些短而精的作品,高度凝练化,人物情感、故事焦点、生活画面以及作品特有的抒情色彩,都通过若干精心选择的画面而凝聚在一起,如王愿坚所言,他是从悲壮历史中提炼出闪耀的诗情,因此,王愿坚的作品篇幅简短,却产生强大的艺术张力,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堪称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名家,红军长征故事写作第一人。
新时期以来转向凝重与沉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征小说,充满了亲身经历者的胜利激情和后来者的崇敬赞美,新时期以来的同类题材,就开始转向凝重与沉思,染上了这一时段文学中特有的历史反思的浓郁色彩,在人物形象设置、主题思想开掘上,都有了新的拓展。乔良的《灵旗》、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央红军长征伊始的血战湘江、损失过半的大挫败作为着眼点的,但是,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又将两部作品引向了不同的方向。《灵旗》写的是一位脱离了红军部队的逃兵青果老爹,对残酷的湘江之战的亲身经历和他流落乡间之后几十年的沧桑变化。敌对的两大政治军事势力的殊死搏杀,和革命阵营内部严酷的自我清洗,以及在历史的狂暴潮流中不由自主地浮沉的人们的命运,这样的思考,跃上了新的高度。故事情节跳跃回环,大开大合,灵光闪现,摇曳多姿。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则是从全景式的场景展开,对红军兵败湘江的前因后果予以冷峻的追索,于是,从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员,到在第一线浴血苦战的普通战士,从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到大战在即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执行,都给予了精心的刻画和描写。这两部作品,都是从红军长征中悲剧的一幕写起,写失败,写逃亡,写历史教训写沉痛回首,这又和刚刚走出10年“文革”的梦魇之际,人们拷问历史、拷问灵魂的迫切心态,相互呼应。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全景式表现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老作家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魏巍高屋建瓴地站在鸟瞰革命运动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战略转移。除了红军基层指战员形象的塑造,小说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不仅写出了他们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抱负,也透过艰苦的战争岁月写出了他们鲜明的人物个性和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心。对蒋介石、王家烈、张国焘等人,也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脸谱化,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深入剖析人物之间的联系,写出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虽然面目可憎,但同样栩栩如生。全书紧张舒缓结合,既有对艰难环境的沉重记录,也不乏诗化语言对征途上美丽风景的描绘,多处可见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与这种沉重的历史反思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写作形成对照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个人化写作”,作品的主人公,在不失其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前提下,个体的经验和情感,占据了作品的表现中心。莫言的《革命浪漫主义》,表现一个参加中越边境作战负伤的小战士,与一位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的有趣对话,老红军讲述的故事,粉碎了小战士从电影中得来的红军长征之高亢激昂高大巍然的情调:饥饿状态中红军官兵的焦虑不安、各显神通、千方百计搞粮食的故事,以及为了破除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挥泪斩马谡,将一时疏忽烧了一间老乡的草棚的红军班长就地正法。莫言在小说中写道,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与虚假革命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人当人看,后者把人当神看。叶楠的《红军轶事》,也写了红军长征中的饥饿断粮,师长指派一个班长去找粮食,并且下了死命令,班长在大巴山里徒劳甚久,好不容易碰到几个当地的农民,但这些农民,不可能向红军班长提供他们自己的救命粮,班长完不成任务、无奈绝望之下,开枪自杀,像莫言笔下的那位被处死的班长一样,显示出军纪与人性的悖论,显示出历史的严酷。傅建文的长篇小说《长征谣》,着眼于个人命运和选择,宏大的长征历史,似乎成了作品中的淡淡背景。身负重伤的红军警卫连长秋水,被迫离开部队,在毛尔盖地区养伤,在追赶大部队无望的情境下,一心要回到家乡去,与自己的妻子团聚,他的妻子却在一心要寻找丈夫的意念下,踏上了尾随红军长征之旅。夫妻两个人逆向而行,各自重新走过红军长征的路途,拓展出有意味的叙事空间,为如何以个人的心灵激活既往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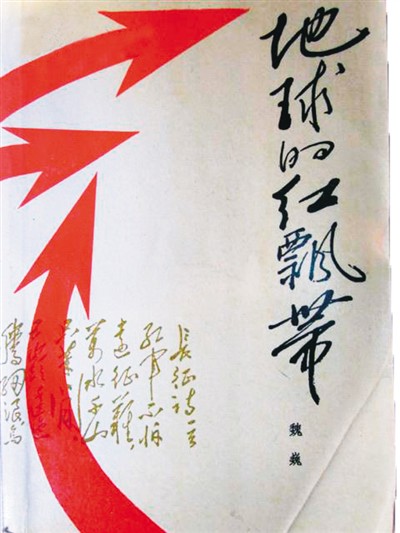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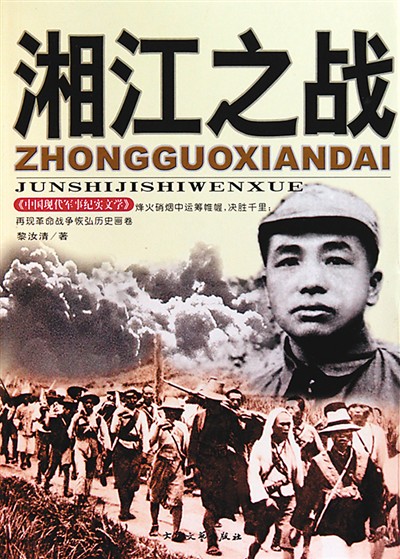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