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丽的国家》,他们这样说:
培养正见的正途不是听同一种人从同一个角度重复说同一种话,而是听不同的声音、冷僻的声音、遥远的声音。在这本书里,一个美国少年,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看我们习以为常的北京、中国。
——作家冯唐
这是一本优美的小说。作者是哈佛大学22岁的学生桑顿。基于作者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经验,本书描述了一个外国少年眼中的东方国家。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其中描写的中国少年的奋斗和命运,引人深思,值得中国学生阅读。
——科学家李开复
异国少年观察陌生国家的潜望镜,用澄澈观察无序,也有奇异的美丽。
——青年作家蒋方舟
我曾从某本书上读到过这么一则运动规律,就是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影响之后发生的事情——球一旦动起来,跟着便会发生一系列预期的且不可避免的连锁反应。抛球、击球、发球完成后,后面可选择采取的动作就很有限了,而且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要不是在北京待的那一年,我一定会驳斥这条所谓的“运动规律”太过宿命论,而且是漏洞百出的。但是,经过那一年,我不再这么肯定了。
波石(他的英文名叫博伟,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冲我笑笑,在伸出手的同时,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名字。
他的发球又快又重,在场地上低低地打滑。在开始的三局里,我几乎很难够上球。波石简直是教科书上“为什么左撇子网球手具有优势”这个论题有力的佐证者。
在比分变成3∶0的时候,我开始逐渐扳回局势。然后由于波石的两次发球失误(他把球发得太远),我破了他的发球局。我对于这片平滑场地开始逐渐感到胜券在握,而波石开始从掉以轻心慢慢变得力不从心。
在比分变成3∶3的时候,我感到波石有意让我的比分更接近。蒋女士(教练)在场地的另一端大声询问我们的比分情况。波石一边回答3∶3,一边朝我挑着眉毛笑了笑。
这难忘的记忆片段,总让我在今后的岁月中不断想起——我意识到,我只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正在把事情搞得复杂。而我倒是很乐意见到他用自己无上的自信心和能力,来戏弄这无常的命运。蒋女士把手背在身后,来到了我们这儿。波石又回到差不多75%的状态。他赢回了自己的发球局,然后我又用Ace球赢回了一局,我怀疑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波石控制了场上发生的一切,他将最后比分书写为7∶5。蒋女士在波石赢下最后一个比分的时候,轻轻点了点头,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
波石是我看见过的最有才华和天赋的选手之一。他在其他的选手中鹤立鸡群,每当看到他那标志性的黄色发带,绑住一头蓬松头发的时候,就仿佛他正居高临下,向这个世界宣战。作为一个左撇子,他把发球牢牢固定在高速状态,而且几乎可以把球发到任何地方。每一发球都把他带近网前至少三英尺,因此波石能够凭借不断的进攻,直到将对手的回击逐渐削弱到无力。然后,他会果断地把球以一种刁钻的角度打到底线附近或者是对方半场任意位置。这种打法无比犀利,他的对手根本没有时间反应。他同时能够在任意速度的球尚未落地之前,即挥拍出击把球接住。我清晰地意识到波石正在用一种能够激发我表现出最佳状态的方式来进行训练。仿佛是他已经掌握了一种可以反转制胜为求败的能力,并且还努力让这一切看起来是仍在尝试。
那天,我们去了麦当劳,尽情享受了鸡翅和摇摇薯条以及可乐,最后以两支冰激凌结束了这顿饕餮。
在这样的一顿午餐之后,我俩谁也不想立刻赶回场地了,因此我们晃晃悠悠地走了回去。我问起波石是如何开始打球的。他说他从小就住在网球场附近。“因为一些球拍很旧了,所以他们允许我们使用。我和邻居街坊的孩子们对着停车场大楼的外墙打上好几个小时,我总是要比他们打得更久些。那里的负责人对我的练球声可能烦透了,所以有一天他就走了出来。那时我觉得肯定有麻烦了,不然他就是想朝我丢鞋。结果他叫我把我妈妈找来,说是要和她谈谈。但是我压根没告诉我妈,因为我怕他告状。结果第二次去的时候,他问我妈妈在哪儿。我和他说,在上班。他便问我肯不肯来上网球班,他说我得把我妈找来签个字……”
“所以你一直很热爱网球?”我又回到波石的问题上。
“一直如此。”他微笑起来,“永远热爱!”说着他也笑出声儿来。
博伟问了他想知道的关于美国的一切。他甚至想知道我们每天听的音乐、看的电影和吃的食物。
自那个下午以后,我开始学着不再直截了当地提问,而是试着让答案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太乐意谈论自己了。如果你只给他们半次机会的话,他们一定会一口气告诉你他住哪儿,儿女和孙辈的名字,业余时间做什么——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养成的,或是出于生存而养成的国民性抑或是保守。我所遇到的中国人都乐意倾听,却都少言寡语。
我俩达成一致,我说中文,博伟就得说英语。我告诉博伟我是如何度过一天的。我会有意识地选择字词短语,好向他描述我周日的出行。博伟认真地听着我和维多利亚(父亲委托他照料我的生活)的各种际遇。和我喜爱这些经历一样,他也喜欢听这些故事。
一次吃完午饭走回来的路上,博伟问如果我不能打网球了会去做什么。我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因为我并不确定自己听懂了这个问题。毕业后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可能不会打球。我也没考虑过在毕业之后,还继续打网球——那样的生活实在是有点残酷。再加上其实我更愿意回国继续高中学业,进而深造。因此我向博伟说起,可能会和父亲共事。总之,答案非常含糊。博伟于是开始自顾自地说起这个问题来。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我感受到眼前的他是如此真实。“我爸爸想让我去做水泥匠。他一点都不看好网球。‘等我站稳了就来教你入行。’他总是和我这么说,但我干吗要停下打球等他?”
在我飞回中国的前几天,我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见了许多朋友,我们玩了冰上曲棍球。他们谈话的主题涵盖了从对繁重的学校作业的抱怨到对漂亮姑娘们的讨论。游戏结束后,我们一帮人拥进专卖店看最新的冰球装备。这些男孩从不顾虑他们要买的东西将会花掉他们父亲账户上多少钱,只要他们想买。虽然他们从未去过中国,不过他们仍旧表达着自己对于中国这个国度的观点和想法,尽管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他们从父亲那里道听途说再照搬来的。他们似乎认为从某种我难以理解的程度上解释清楚了一切,而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对他们说的一些进行回应,甚至只是尝试层面上的,也让我不知道该从何处进行。在与博伟、白建明、郭峰、常洋和李达在一起生活的4个月后,此刻家乡的朋友们说的仿佛已是令我陌生的外文。家似乎比我离开时更加遥远了。
1月10号,我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我参加了训练。读懂所有男孩的内心情感是困难的,不过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的归来。当我从包里拿出球拍时,博伟走过来说:“我帮你想了个中文名。”
“嗯,好啊,是什么呢?”
“禹。来自于‘大禹’这个名字。他生活在4000多年前,因为坚持不懈和果敢坚定而被人们铭记。”
“好吧,我不知道这名字是否适合我,我得先想想。”
晚饭后我上谷歌寻找大禹生平,“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一则体现禹奉献精神的传说故事。我可以体会博伟为何如此钦佩大禹了。正如这个古代形象一般,博伟也总是时刻准备着给予别人一切他可以付出的。我曾见证过他在整个秋季训练中为队里的男孩们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精力和时间。他不断把他们从对蒋女士的抵触心态中解救出来。他使他们在前来拜访的网球选手中表现出自己的闪光点。他给其他人一种仿佛他们可以无限发挥出自己潜能的感觉。
“我们应该在6点之前到那里。”维多利亚说。
“6点,早上吗?”
“最好的东西只在早上摆出来,等到9点的时候所有好玩意儿都被拣走了。游客们等到下午才来。”维多利亚提到了一家叫潘家园的大型集市。除了给弟弟找一些军事方面的东西以外,我想给妈妈带点东西。
此时,外面的天还是黑的。维多利亚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手电筒。“这里走。”她说。瓷器,陶器,皮革,牛铃铛,硬皮钱包,甚至还有老旧的木质洗衣板,这些杂七杂八的收藏品都被随意地摆放在几片又脏又破、不规整的布上。“这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东西。”
维多利亚用她的手电筒照着路。大多数小贩都蹲着,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他们就马上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些不值钱的廉价小饰品,然后告诉我们“真的真的很物超所值”。
维多利亚在一个货摊前停下来,摊子上摆着一套形状不同,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圆形的小碟子。上面画着深粉色的牡丹和亮绿色的叶子,摆放在一个破旧的天鹅绒盒子里。当我蹲下来的时候,摊主递给维多利亚一只绘成同样风格的笔筒。这跟以前我妈妈用来做花瓶的那只简直一模一样,所以我朝维多利亚点了点头。这个小贩明白了我要选择这只笔筒,但是他很不好说话。最后我用200块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30元买下了这只笔筒。维多利亚觉得这太贵了,但是我对我买下的东西很满意。“下次你先走开,说不定可以花70块买下它。”
我们顺着一排又一排的小摊走下去,其他的顾客也开着手电筒在逛。看起来好像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消失了的部落在地上遗留下来的踪迹。终于有不寻常的物品映入了我的眼帘,跟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饰品和陶器瓷器的碎片摆在一起的,是一个一面有红星的绿色头盔。“别表现得很感兴趣。”维多利亚用英语跟我说。
蹲在毯子后面的男人站起来,把那顶头盔塞给我。“你喜欢吧?便宜点给你。”它很沉,头盔上面有遮光板,我往上推了一下然后举到头顶戴在头上。我知道如果我把它买回去送给我的小弟弟,他会把我当英雄看待的。维多利亚站到了我的前面。
“这个多少钱?”
“三百块。”
“太贵了!一百块!”
“这个真的是军用头盔,两百块!”
“一百五十块!”
“不可能!”
“那好吧,我们走了。”
“好吧!好吧!一百五就一百五!”
他把头盔装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扯住我的衬衫,示意我等一下。他拿出一个红色绳子扎住的小硬纸板盒子,盒子里面是四枚勋章,红色的那块缎带很脏,皱皱巴巴,斑斑点点,勋章的光泽早已不再。
我问他,“这是你的吗?”
“这是我父亲的。”
我接受了他给出的第一个价格。我觉得一个男人沦落到要贩卖他父亲在战争中获得的勋章的地步,那么他一定是处境困窘,如果这时我讲价的话看起来会很不道德的。当我们走开后,维多利亚告诉我,我多花了三倍的价钱。“你真是有一颗柔软的心,这是好的,可是这是奢侈品我们消费不起。”
我给吴师傅看那顶头盔跟勋章。他把他的手伸出来翻看那顶头盔。“非常少见,成为一名飞行员非常难,要通过很多很多的测试。只有少部分人才能通过。最优秀的人才。”我给他看那些勋章。他解释说这是旧时中国国民党军队对勇者的嘉奖。他用汉语说了些什么,我不是很能理解。我问维多利亚,“他说,‘保管好这些东西,它们沾满勇气’。”
我一回到美国,感觉就像进入了另一个色彩斑斓的国度。家里的草坪是碧绿的,天是湛蓝的,云是雪白的。我以前从没有意识到身边有这么多花,而春天的晚风带来的花香是多么惬意。过去的一年我自己做了无数顿饭,这次回来很想把自己的秘方同父母兄弟分享。
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中国人更明白生存之艰辛。大多数美国人从不担心能否找到工作,是不是能在某个地方扎根下来。而在中国,大多数人觉得生存本来就是艰辛而险恶的,勤劳工作也不一定代表你有坚韧的品格。
我在家里待了一周,然后去佛罗里达的国际网球学院参加夏季训练。见到旧日的教练和队友让我觉得舒服而熟悉,有时候选择不去知道太多背后的故事反而让生活变得轻松。我曾经痛恨的五英里跑和在北京跑楼梯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现在总是能跑第一。有一阵我很享受这样的变化,但马上我就想念起北京的那五个队友。我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还记得和他们因为三个贵州人的故事疯笑。我多希望他们能有机会来这里看看,尤其是博伟。
作者简介:
约翰·兰多夫·桑顿(John Randolph Thornton),1991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2岁移居美国。7年前,身为银行家的父亲、一位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清华大学教授约翰·桑顿先生和14岁的儿子约翰·兰多夫商量,让他去中国游学一年,学习汉语并与北京网球少年队共同参与训练,他一个人来到中国。回到美国后,桑顿于伊顿公学的霍奇基斯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目前在哈佛大学就读三年级。
在哈佛就读期间,桑顿对汉语的掌握进一步提高,并师从 Amy Hempel及 Bret Anthony Johnston 学习小说写作。不久前,桑顿因其创作的以美国南部为背景的短篇故事集而被授予男爵罗素布里格斯小说奖,并获得艺术进步奖学金。
历时4年,约翰·兰多夫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经历写成了小说《美丽的国家》。
《美丽的国家》小说梗概
14岁的美国男孩 Chase,独自来到北京学习普通话,并在北京少年男子网球队接受训练。在父亲指定的中国朋友维多利亚带领下,他每天上午上中文课,下午参加网球训练,节假日参观故宫、去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宝、到798艺术区走访画室。Chase和网球队里最有天赋的男孩Bowen建立了深厚的友谊。Chase看到Bowen受到新旧中国价值观的冲击,在墨守成规和别创新格中的纠结——而这些都抑制了Bowen 作为一名职业球手的发展。Bowen 对一切与网球相关事物的强烈求知欲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有一次他被逮到闯进电脑室下载世界级男子网球选手的比赛并因此被踢出了球队。回到美国后,在奥兰治杯国际青少年锦标赛上,Chase发现Bowen由于年龄问题陷入纷争。Bowen看到Chase后寻求他的帮助,然而Chase 却因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原因消失在赛场。在其后几年时间里,Chase一直为没有在朋友绝望之际伸出援手而深感自责。2008年奥运会之际,Chase再次来到北京并打听 Bowen的下落。目睹Bowen和他的父亲在老家天津打着散工,他内心纠结于该和Bowen说些什么。最终,Chase选择默默地离去。
这一年,Chase对友谊和中国文化不断认知,更加理解勇气、同理心以及责任心这些概念的内涵。在中国的日子,伴随着他多方面的成长。
(刘莉 何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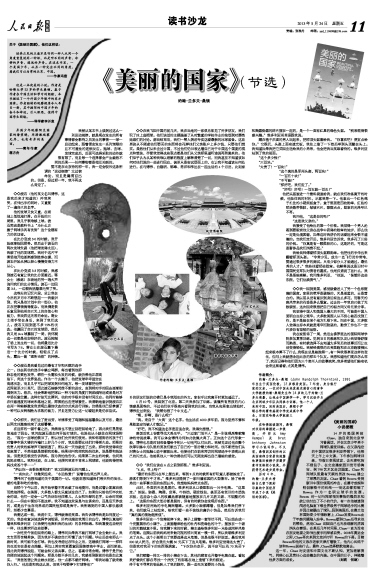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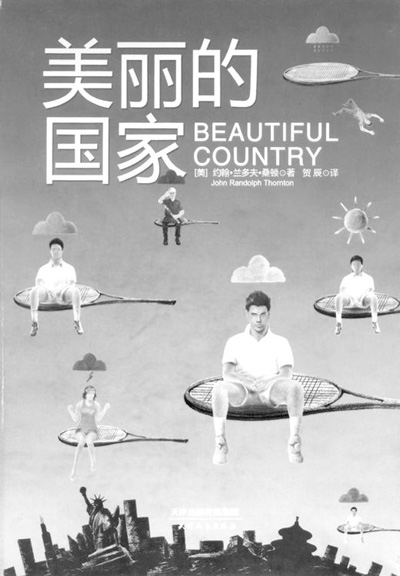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