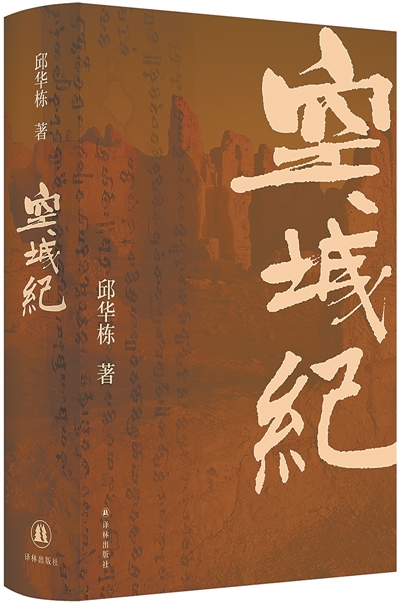书写西北大地上的故事,作者在心理上有着天然优势。同时,他热衷于研究历史文化,《空城纪》就来源于对历史蛛丝马迹的想象与虚构书写。这种基于史实的虚构,在赋予历史以温度的同时,又使其有了深刻的当代意义。
关注邱华栋的创作很久了,30余年来他写下1000多万字作品,诗歌、小说、影视、文学研究等都有他的身影。最近读到《空城纪》,我认为这是有个性特点的一部作品,不仅对他个人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当代小说创作也有启发意义。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北京之于老舍,高邮之于汪曾祺,苏南之于高晓声,都是生长出文学森林的沃土。邱华栋生于新疆昌吉,在那里度过童年,这一次,他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西北。书写西北大地上的故事,作者在心理上有着天然优势。同时,他热衷于研究历史文化,《空城纪》就来源于对历史蛛丝马迹的想象与虚构书写。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分别被不同故事“复活”,这种基于史实的虚构,在赋予历史以温度的同时,又使其有了深刻的当代意义。
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要用什么样的写作姿态、语调讲述历史?这是历史小说面临的叙事伦理问题,也成为进入《空城纪》的阅读路径。如第一章“龟兹双阕”,分别以汉代和唐代的两种音乐和两段人生展开叙事,作者从文化传承角度起笔,辅之以鲜活故事,让小说生动起来,成为足够有趣的“历史科普读物”,从多个维度启发读者思考。
首先,小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第一章的3个故事为例。在“琴瑟和鸣”中,弟史公主和绛宾的爱情贯穿着音乐文化,他们的婚姻呼应了民族融合的大命题,二人对音乐的传承与热爱,体现了文化交融的过程。第二段故事中,作者用同样手法塑造了两位龟兹音乐人:吹筚篥的白明月和弹琵琶的火玲珑。故事中的人物以音乐相聚,每一个人都用音乐为盛世添砖加瓦,展现了唐代时期的民族包容。第三段虽是当代故事,但是在地域、民族等方面,作者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处理。“我”是一个民族乐器收藏者,另一个主人公王雪毕业于音乐学院,热爱琵琶弹奏。阴差阳错中,“我”在龟兹遗址上找到了一把残破的琵琶,这一古物又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整部《空城纪》几乎都在不同历史空间中延续这样的结构,蕴藏了民族融合的历史。
其次,在对历史的叙述和想象中彰显人的价值。《空城纪》体现了一种“博物馆写作”,大量知识和历史典籍浓缩在一起,处理不好会冲淡人物形象。小说巧妙地在不同时代选取故事,主人公的命运也是时代的写照。如第二章“高昌三书”讲述班固、班超的故事,这些在历史上留名的人,既是时代成就了他们,也依靠个人的选择和努力。作者细致处理二者关系,没有简单地将人物命运归结为时代,也没有夸大他们的选择和努力,甚至一些细节描写还突出了人物的复杂性。于是,寻常人生甚至很小的事件连同主人公的感受,一同赋予小说以史诗品质。
再次,对话型的复调结构较有新意。《空城纪》是当代与历史的对话,是“我”与“他”的对话,是物与人的对话,也是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汉唐故事如何与当下产生连接?历史小说的内容可以虚构,但“时间”的基础却是历史的、真实的,因此作品故事很容易徘徊在历史中。而一部小说的首要任务,是要有自己独特的时代属性。《空城纪》具有这样的特点:“尼雅四锦”主题是汉代丝绸,“楼兰五叠”揭示楼兰历史变迁,“于阗六部”在出土文物基础上生发想象……作者的做法较为直接——用当代生活连接汉唐故事,以一把琵琶,接续了活在当代的我们与历史的关系,虚构出一个开放的历史时空。这个开放空间是小说与历史的互文,能够把有声的历史转化为有情的历史,提高作品的文学性。
《空城纪》对小说结构做了新鲜的探索,由多个短篇组成中篇,进而连缀起来合成一部交响乐式的长篇。每个声部都有自己的回响,雄浑处有清新,委婉处有高亢。作者把它称之为石榴结构,虽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事件,但由许多石榴籽紧密拥抱组成。这种小说结构,西方评论家称之为“中国屏风式”结构,推开一扇,又一扇展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红楼梦》就具备这一特点,作家王蒙发现,《红楼梦》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阅读,而没有任何突兀感。对读者来说,《空城纪》也可以从任何一章开始阅读。或许,这正是作者多年研读《红楼梦》获得的一种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