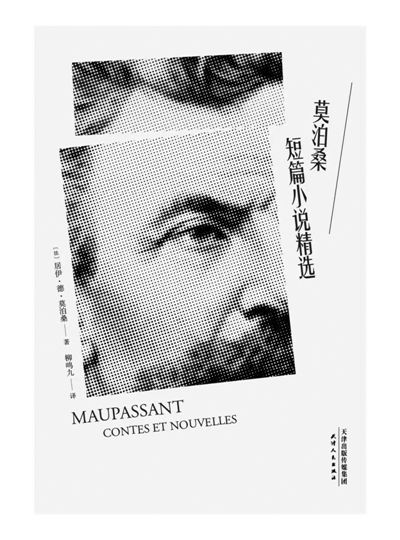我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渊源,还得从大学时代说起。记得那时法文精读课和泛读课中,都会选一些莫泊桑的作品。那些真实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有几乎完美无缺的布局谋篇,有深刻的对人情世故的洞察与针砭,语言风格又是那样纯净清晰,给读者一种顺畅舒适、亲和平易而又色彩缤纷的语境。对当年的我们来说,这不仅是语言文化的滋养,也是审美的范例与召唤,恐怕没有人不曾向往过成为莫泊桑小说的译者。
这圆梦之路一走就是40多年——因身居研究岗位,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主编《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时,才亲手翻译出几篇莫泊桑小说。令我意外又欣慰的是,在莫泊桑译本林立的情况下,不止一个外国文学选本采用了我的译文。此后几年里,我在研究之余陆续译了一些短篇,最终结成近30万字的选集。于我而言,译介莫泊桑的最大愿望就是将他卓越的小说艺术传达给普通读者,能在十几年间一版再版、成为经得起时间淘沥的“长销书”,或许也是对“生命之树常青”的一种诠释。
“一个字适得其所的力量”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300余篇的创作量在19世纪法国文学中堪称绝无仅有。他在短篇中描绘的生活面极为广泛,实际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一幅全面的风俗画。左拉曾经这样评价:“每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但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觉醒悟的生活窗口。”更为重要的是,莫泊桑通过叙述故事、呈现图景、刻画性格,将短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说到莫泊桑的语言艺术,“白描”总是被第一个提及。实际上,以丰富鲜明的色彩绘制出精细入微的图景,也是他的才能所在:在家喻户晓的《羊脂球》中,为了揭示那些“上等人”的馋嘴、自私与厚颜,莫泊桑将羊脂球那一篮子美食描写得似乎能闻其香、能见其色、能知其味,让读者也为之心动;他又细细地描写了普鲁士军官嘴上的两撇胡子,让人似乎看到“稀到最尖端只剩下一根根极细的黄丝”,给读者留下一幅讽刺画。
莫泊桑摒弃华丽的辞藻,他的语言清晰、简洁、准确、生动,像一池透明的清水,不仅与他精炼的叙事方式相得益彰,在写景状物上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对于诺曼底的山川平野、小镇情貌、田舍风光、渔家景致、巴黎街景以及朝暮晦明的自然景色,莫泊桑都进行了卓越的描绘,留下一幅幅构图清爽、色彩鲜明的画面。
莫泊桑在《论小说》中这样阐述他理想中的文学语言:“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字最能表现它,只有一个动词最能使它生动,只有一个形容词最能使它性质鲜明。”换言之,他追求“一个字适得其所的力量”。
翻译中的“油盐酱醋”
用得其所,一字千钧。这句话适用于写作,也适用于翻译。优秀的文学译本,至少本身就应该像一部文学作品;优秀译本的文字,首先就应当是经过不着痕迹的修饰、经过反复锤炼的文学语言。惟其如此,才能给予读者美的阅读体验。
许多读者说我的译本“句子圆润没有翻译腔调,如同自己所写”,有的也认为“与原文有所游离,有所增减”。倘若翻译的文字有色调,我承认自己在翻译中常常要对色调的轻重、浓淡做点自己的手脚,用俗话说,就是如何添加“油盐酱醋”。但这绝不是在烹调中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添加作料,让一锅清淡的高汤变成浓油赤酱,而是要先拿准文学作品的全篇精神,再决定分寸与手法。
以莫泊桑的《月光》为例。作家借助这个顽固神父被月光下少男少女的爱情打动、震撼的故事,把月夜写得温和、柔美、浪漫,还使它诗意地解决了人间的纠葛与矛盾。我译这篇小说时,一方面注意保留这月夜美景的柔和色彩,千万不可妄自添加浓油赤酱,一方面则尽可能选择最优美的语言来译述每一处,哪怕是原文用普通词句一笔带过的细节。例如神父自问的一段话中,我将“为什么最善于歌唱的鸟雀不像同类一样休息,而是在令人心生动荡的阴影中歌唱?”译为“为什么歌唱得最美妙的鸟儿,偏偏不像同类那样在夜里安睡,而是在撩人的月影中欢唱?”以我之拙见,莫泊桑自己也被这月色所感动,甚至是在以自己的笔力挑战实际的夜景,留下一篇与自然之美分庭抗礼的小说,我这“与其美得不足,不如美得有点过分”的译文,想必不会让这篇杰作“跌份儿”。
好的翻译是进入“化境”
怎么样的翻译算得上是好的翻译?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信达雅”。这是《天演论》译者严复在19世纪末提出的理论:“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百年以来,信、达、雅三大标尺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但也伴随着关于翻译标准的持久争议,例如,对“直译”“硬译”的过分强调就导致了对“信”的绝对盲从。
在我看来,对“信”的绝对盲从、对原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雅”和“达”的忽略与损害,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力主求“信”,实际上只得原文的“近似”,字面背后的思想、感情、声音、节奏,就不容易传递。把“信”“达”“雅”三个标准单独化、独立化,必然带来翻译工作中的局限性。
2017年,我组织了“译道化境论坛”,邀来10多个语种的近40名翻译家共同探讨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新标准。我们颇为推崇的是钱钟书的“化境”说。按照钱钟书的说法,“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钟书同时指出,彻底的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但“化”不可实现却可追求:面对着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透彻。然后,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译文的修辞意图和审美追求需要符合原文的形态与意念。这种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态依然故我。
照此说来,好的翻译实践,不是别的,就是进入了奇妙的化境。“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也是中国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
柳鸣九,193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柳鸣九文集》(15卷)、《法国文学史》(三卷本)等著作、译作40余部,散文集《种自我的园子》《巴黎对话录》《友人对话录》,编选组译《萨特研究》《加缪全集》《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等,主编《盗火者文丛》(十卷本)、《本色文丛》等。2018年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