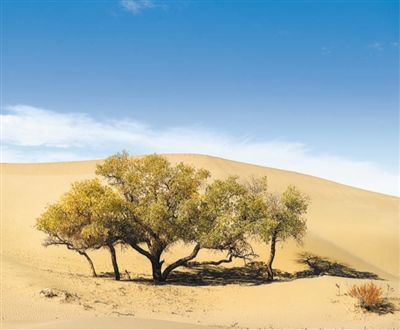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一夜的戈壁滩很冷。炉膛的火苗跳跃着,把铁皮做的烟管烧得通红,坐在炉子上的铝壶在夜里依旧欢快地唱歌。
临睡前,我将一壶冷水坐在炉子上,无烟煤在炉膛里呼呼地燃烧。无人搭理的水壶自己在后半夜烧开了,便自顾自鸣唱,四周水蒸气弥漫。在戈壁滩上寒冷、干燥的冬夜里,一壶滚开的水就是房间的加湿器,这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洗漱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却听到隔壁女兵们在唱熟悉的军歌:“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我也是十八岁参军来到河西走廊的。后来我在团里的军人俱乐部当主任,手下四个年轻女兵,住在我的隔壁。每晚临睡前,我像帮助小妹一样,帮她们加好煤,封好炉子,再在炉子上坐一壶水。女兵们不明白个中道理,向我抱怨那个铝壶半夜鸣叫,她们一夜没有睡好。我说,铝壶在夜里唱歌就是妈妈的摇篮曲。她们却笑着说,自己已经不是流鼻涕的小孩了。
那晚直到后半夜,我依旧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唱歌,歌曲一首接着一首,朦朦胧胧。后来愈来愈真切,是女兵们在夜里唱歌,是压低声音在唱的。
天亮后,住在我隔壁的女兵们就要退伍回老家了。那夜是她们在团里的最后一晚。
陡然,铝壶停止歌唱,已经老朽的壶底传来“咯嘣”一声。我醒了,知道壶里的水快要烧干了。我起来加水,听到那若有若无的歌声依旧执拗、倔强地从隔壁屋子传过来。我用火钳子勾开一圈一圈的炉圈,“当啷”的声音很响,“哐里哐啷”加煤,用火钳子捅开炉子。房间里的铝壶续了新水不再鸣唱了,隔壁屋子的歌声也戛然而止。
我默默喝水,猜想隔壁屋子女兵们这会儿也许在听我房间的响动。过了一阵,她们听见我房间没有动静,歌声又响起来,还是那熟悉的军歌。
我一个人静静坐着,看炉膛里的火苗慢悠悠蹿上来,红红的火焰舔着乌黑的铝壶,沉沉的铝壶开始有了响动,“吱”的一下,接着慢悠悠扯开了嗓子。歌声和着铝壶的鸣唱,又开始清晰地送进我的耳朵。
那一夜女兵们的歌声有点特别,和站哨的士兵夜里用粗糙的嗓子唱歌不一样,柔软牵肠,如一泓清泉慢悠悠流淌,一朵洁白的云彩缓缓飘移。
我坐起来在屋里踱步,尽量不发出声响。看来,今夜,我肯定是睡不着觉了。让她们尽情唱吧。
我用手在黑暗里打拍子。女兵们唱的是《当兵的历史》:“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尽管隔壁屋子女兵们唱歌的声音压得很低,在夜里我还是听得真切。差不多也是十八岁的年纪,这些女兵们移防到塞外军营,当时是我去接站的。她们一下火车,就被祁连山下十月的寒风打了一个跟头。女兵们住在我隔壁房间里,夜里炉膛的火灭了,冻得她们蜷缩着不肯出被窝,几个人在夜里唱歌,拼命用手擂我的墙。我披着军大衣顶风过去给她们引火。
第二天,我教她们如何在临睡前封炉子,才不至于炉火在半夜熄灭。她们学会了,但年轻人瞌睡多,一觉到天亮,因为没人加水烧坏了几个水壶后,她们便不愿再在炉子上坐水。她们的借口是,她们已经听惯了我在隔壁房间里咳嗽、喝水、看书、朗诵,听我房间的铝壶整夜的鸣唱,不需要再放一个壶在炉子上面了。
后来,女兵让家里寄过来一个加湿器,放在房间里。那夜临睡前,加湿器已经送给我了,她们说这是分别时送给我的礼物。
天开始泛白,女兵们在唱《战友之歌》,歌声非常整齐:“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战友,战友!这亲切的称呼,这崇高的友谊,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钢铁集体……”
我在屋子里和着女兵的歌也在低声的合唱:“战友战友,目标一致,革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同休息,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
隔壁的女兵歌曲接龙:“战友,战友!为祖国的荣誉,为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并肩战斗夺取胜利,夺取胜利!”
我的泪水挂在腮边。
是的,这些移防过来的女兵们,很快就适应了戈壁滩上的恶劣气候。她们也爱美,偷着改肥大的军裤,让我训得满脸泪花。她们的坚强与乐观超出了她们的年龄。
她们也经常向我抱怨,皮肤粗糙了,嘴唇干裂了。当真正要离开的时候,她们却万般不舍,一夜未眠,唱歌到天亮。
清晨,欢送老兵的火车站台上歌声一片。军歌嘹亮,声音大得让人听不见火车汽笛声。哭红眼睛的女兵们向我敬礼,然后和男兵一起唱军歌。火车站的军歌和昨晚女兵们唱的军歌不太一样,有男兵加入的军歌显得雄壮激昂。
四个女兵站在月台上,大方地唱起《相逢是首歌》:“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现在想起那夜女兵们唱了一夜的军歌,熟悉的旋律仿佛就在昨天。
今年“八一”节,女兵们相约在一起聚会,她们发视频给我这个老主任。她们在聚会上一起唱歌,唱的依旧是那首《战友之歌》,还有那首《相逢是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