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二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与制约,甚至干预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去留。从而实现了唐代国家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沟通与互动。
【摘要】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二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与制约,甚至干预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去留。从而实现了唐代国家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沟通与互动。
【关键词】唐代 乡族势力 地方政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乡族势力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管理
所谓乡族势力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社会阶层:一是有文化的士人。包括科举落第的乡贡进士、乡贡明经之类的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在城市立足,只好回到乡村。还有就是没有取得乡贡资格和无意仕进的读书人。二是致仕官吏。唐朝有退休制度,官员到了规定的年龄就要告老还乡。一般来说,高级官员即使退休也大都居住在城市,或者住在郊外的别业、别墅内,然中下级官吏多是返回乡里居住。三是乡县胥吏。主要指州县政府中的吏职,即九品以下的所谓流外官,即地方仓督、录事、佐史、府史、典狱、门事、执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以及军府旅帅、队正、队副等,此类人员基本来自于乡村,不服役时均活动于乡里。四是乡村豪民。主要指富民阶层,包括大小地主、耆老、侠义之士、强宗大族等。其中耆老是指年老德高、具有一定威望的人员,强宗是指乡村中具有较大家族势力者。在唐代很多村落都是聚族而居,或者同姓之人甚多,因此多以姓氏命村名。也有两姓之村,白居易描写的朱陈村就是“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当然也有杂姓之村,但其中必有一二家是大户,势力超过其他诸姓,也形成了一定的乡族势力。
乡族势力参与地方政治,实际上就是指对乡村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主要包括:第一,乡村经济事务的管理。比如评定户等,以确定缴纳赋税的多少;清查荒田;处理土地纠纷;督促赋税缴纳等。这些都是受官府委托,是服从国家管理的行为。第二,处理乡村纠纷。乡族势力没有司法权,但对乡村中的各种纠纷却往往拥有调解权。由于其在乡村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对于非刑事类的纠纷,乡民往往自愿找其调解,而不去向官府申诉。第三,发展乡村教育,敦化风俗,宣扬道德。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乡校普遍存在,既从事教育,又是人们评议本乡之政的场所。唐代在州县官学之外的乡村,有不少类似于私塾的小学堂,大都由乡族势力兴办,用于教育本乡子弟,宣扬道德教化。唐玄宗甚至下令,命各乡大力兴办乡学,善择师资。乡族势力还举办义事,如救济贫困,治疗疾病,资助丧事等。这些都有美化风俗、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作用。第四,兴办公共事业。比如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桥梁等。在唐代乡村中,乡族势力还出面组织一些互助性质的组织,以处理一些个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务,如礼佛、赛神、庙会、祭祀、救灾、生产等。这种组织叫社邑,在敦煌地区普遍存在,其实在内地也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资料散失,不为大家所熟知而已。第五,保卫乡里。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社会动荡时期,由乡族势力出面组织武装,修筑工事,以抵御盗贼骚扰,叛军烧杀,在边境地区还有防御异族侵扰的作用。唐初著名将领程知节、苏定方、郭孝恪等,早年未入仕当官前,都出力保卫过本乡的安全。第六,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唐朝有许多地方性的礼仪活动,比如迎接敕使、举办乡饮酒礼与敬老仪式等,往往都有乡村耆老与正长参与。有时地位还十分重要,如每年举办乡饮酒礼时,以刺史或县令为主人,设宾、介、众宾等席次,以乡村德高望重的老人充任。举办当天,主人要到宾、介家中再次邀请,宾、介到时,主人要在门口迎接。主人还要向宾、介、众宾分别敬酒,仪式结束时主人要送宾、介、众宾到门口。举办的地点是当地学校。总之,通过一套比较复杂的仪式,以宣扬尊长养老、孝悌爱戴的道理,培养与弘扬良好风尚。此外,乡族势力还有向基层民众宣传官府政令、选贤举能的责任。
乡族势力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及改善吏治的作用
有唐一代,乡族势力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以及在改善吏治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褒扬清廉之官,树立良吏典范。地方耆老对当地官员清廉与否拥有很大的评议权,其方式大约有三种:一种是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反映,如懿宗时的宰相徐商曾在襄阳任节度使,由于爱惜民力,故深受百姓爱戴,于是治下七州父老遂将其事迹整理成材料,赴京奏闻皇帝。晚唐时期福建王审知、陈州赵昶等人,由于劝课农桑、大布恩惠,都先后被当地耆老奏闻天子。也有的是耆老与当地将吏共同奏闻皇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当地父老向监军使、巡察使或者向上一级官员反映,请其代为上奏天子,要求褒奖这些官员,对象有节度使、刺史、县令等。因为百姓并不能直接向皇帝进奏,故前一种方式类似于上访,只不过不是告状,而是反映官员德政而已。监军使、巡察使等拥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能够更加迅速地直达天听,故很多时候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第三种方式即刻德政碑、建生祠。在唐代为地方官所建的德政碑甚多,这一点在宋代成书的《文苑英华》中多有收集,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当地父老所为,有集资雕刻的,也有与当地基层官吏合作建立的,还有就是请求上级官员或皇帝批准为某人立碑或建生祠。如狄仁杰曾在多地任地方官,所到之处皆有百姓为其立碑,建生祠。他在魏州任刺史时,百姓受其恩惠,遂集资建了生祠。有一则故事说,狄仁杰不善饮酒,每年祭祀时节,其上朝时都面红耳赤,武则天感到很奇怪,派人到魏州调查,才知道了其中的缘故。当然这种故事是乡野杂谈,反映的却是民间对狄仁杰的爱戴之情。后来狄仁杰之子也在魏州任职,施政残暴,当地人遂毁掉了其生祠。以上这些行为实际上对官员的考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表面上看,仅仅与德政教化有关,然而却间接地影响了地方官的升迁。唐朝每年都要对官员进行考课,而来自民间声音所形成的社会舆论,会极大地影响官员的考课等级,从而对官员任满后的升迁发挥积极作用。
其二,干预地方官员的去留。由于乡族势力代表地方基层利益,自然关心当地官员的优劣。在唐代有不少文献都记载了地方父老组织民众请求某些官员继续留任,大体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诣阙”请留,就是派出代表赴京请求皇帝把本地任满即将离任好官继续留下来;一种是当地父老率领大批百姓在离任官员必经道路上进行拦截,劝其暂留,然后再向上级或皇帝提出请求,希望其继续留任;另一种方式就是在官员即将任满时,当地父老请求一些士人撰写表章,并设法呈送皇帝,在《全唐文》中此类代某地父老请留某人的表章就有不少。这些做法干预了官员的去留,而且往往能够成功,因为皇帝对社会舆论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也是所谓顺应民意之举。如苗晋卿任魏郡太守任满,改任河东太守兼采访使,当地官吏百姓,有的诣阙请求,有的遮道挽留。淮南节度使崔圆任满赴京觐见皇帝,“耆耋泣诉,吏人遮道,即日诣阙,乞留者三百余人”。当皇帝同意大家的请求后,“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欢欣鼓舞的心情可见一斑。有一种现象,即有些官员因故不愿离开任所,也会操纵一些父老提出请求,从而得以继续留任。也有遮留不成功的事例,如襄州刺史靳恒迁陕州刺史,办理交接手续后,当地父老、百姓拦车塞路,老幼啼呼,不愿放行,每天只能行五里路,一连十日。虽然最终没有留住,但这种状况的出现,对靳恒个人的政治前途无疑是有好处的。有唐一代,在官员任用方面始终关注民意,如唐初齐王李元吉任并州总管时,为政不法,欺压百姓,被免去了官职。后来有人操纵当地耆老赴京请求,遂又恢复了原职。其实唐高祖并不真心罢免李元吉,只是迫于民意不得已而罢之,因为有耆老诣阙请求,于是顺水推舟,便又将其官复原职。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也显示了地方耆老在决定官员去留上的重要作用,即使皇子亦不例外。在唐代还出现过截取外地官员到本地任职的现象。如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当地父老百姓听说王潮为官清明,“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请留”。即请王潮担任泉州刺史。还有一种情况是听说某人贤明,于是耆老与相关吏人共同上奏朝廷请求其到本地任职。如于知微历任道、利等州刺史,政声甚好,果州流溪县丞与当地父老遂赴京,恳请调于知微到果州任职。皇帝感于果州百姓的真情,同意了其请求。
其三,朝廷主动向当地父老征求对官员的意见。地方官员治下的百姓对其治绩如何有切身感受,也最有发言权,因此唐朝政府也会设法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如每年派遣监察御史分巡诸道,号称巡按使,事务繁忙时,还会派精明强干的官吏充当支使,其任务有六条,其中之一就是“察官人善恶”。他们往往会向当地父老询问,或者接受百姓的投诉,年终返京后再向皇帝汇报吏治情况。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唐前期每年还派出诸如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采访使等使职,了解各地吏治情况,他们也都会注意倾听当地父老的反映。据《册府元龟》载:唐文宗时,中书门下专门向皇帝奏请,要求凡刺史离任一月后,委派各州上佐,即长史、别驾或司马、录事参军,“各下诸县,取耆老、百姓等状”,即听取乡族势力对离任刺史工作的反映。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社会中乡族势力的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地方官员形成一种制约,乡族势力不仅成为中央联系基层的纽带,而且还是地方民意和社会舆论的主要代表。
乡族势力在乡村治理与整顿吏治方面的历史镜鉴
唐朝前期国家权力已经下沉到乡村基层社会,通过建立里正、村正等乡官系统,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管理。唐前期均田制的实施,再加上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政策的推行,保障了小农权益,使得社会稳定发展,也使唐朝逐渐迈入了盛世。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逃户大量产生,尤其是安史之乱引起了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乡村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富民阶层为主的乡族势力不仅掌握了乡村经济资源,而且力图谋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逐渐发展成为基层社会中最活跃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里正、村正等国家选派的行政人员已无法控制变化了的乡村社会,甚至沦为无人愿干的苦差事,国家为了将基层资源输送上来,又把连带责任强加于乡官之身,迫使其要么加紧盘剥农民,要么自行逃亡,导致唐代的乡村治理陷入了困境。两税制的实施等于承认了富民阶层在乡村中的地位,标志着唐前期乡村治理体系的终结,通过赋予其更多的行政职能,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这种治理模式的特征,就是将原来以官(乡官)治民,改变为以民(富民)治民。乡村富民既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又是政府代言人,管理乡村事务,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到了缓冲调节作用,使得乡村结构逐渐稳定下来。此外,以富民为主的乡族势力又承担了许多乡村公共事务,从而解除了政府想做又做不好事务的困扰。同时,国家又借助乡族势力强化对地方官吏的监督,这种监督比从上而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更加有效,可以促进吏治的改善。这就是自唐中期以来直到明清时期,历代均沿袭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
在国家建构下的乡村治理有三大职能,即维护稳定、汲取资源和公共服务。在中国历代社会中,前两种职能得到了极大关注,而后一种职能不断被弱化。实际上公共服务职能是维系前两者良性运转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汲取资源力度过大,就会导致乡村衰败,破坏社会隐定。乡族势力取代原有乡官体制后,至少乡村公共服务的职能得到了很好地履行,减轻了国家的责任与负担;对地方吏治的监督又形成了对地方官员权力的制约,使其不敢罔顾民意,率意妄为,有利于吏治的改善。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②[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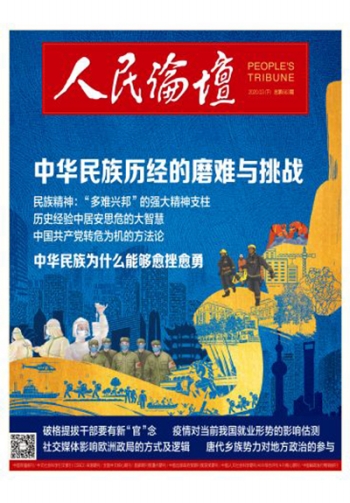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