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面向全国百万公安干警视频培训专业执法的一招一式。其中,“面对群众围观拍摄,如不影响执法民警不得干涉”的说法备受关注。在执法现场,警察权力如何行使?公众权利如何保障?似乎是警方先“退了半步”。
头顶上是早就排布整齐的“天网”,这边警察刚打开执法记录仪,对面的群众已打开一溜摄像头……脑补了警民互拍的“掎角之势”,虽不陌生,但如果在大街小巷铺展开去,依然觉得滑稽又沉重。这是警民的“平衡”,也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彼此凝视,这是个法治议题,更是个有关权力的政治隐喻。
200年前,英国政治学者边沁曾构想一个全景敞式的环形装置。在这个装置中:处在环形边缘的人,彻底被凝视却看不到别人;处在中心瞭望塔的“权力”,被感知到在凝视一切却不被发现。边沁将这种不对称的装置视为高效轻便的权力运行模式。在边沁年代,这样的物理装置,并无对应实物,更多是盘旋在大脑中的政治模型。
历史轮转,构想成真。无论中外,街头密布的监控装置已成警方最简捷的工具:震慑效果显而易见,破案率大幅上升,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技术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但问题似乎随之而来:当大家不信公章信摄像,权力似乎也凝结在了技术身上。雷洋案中,监控“没开”、执法记录仪“毁坏”,警察执法公信力也因此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没视频,你说个XX”。不知不觉中,权力的公信力凝结在技术上,就像露水凝结在初秋的早晨那样自然。
技术的确改变了权力结构。正如互联网的兴起对“知识垄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个公众的摄像头,甚至胜过法官的几十页判词。警察凝视着群众,群众也凝视着警察;你为执行法律记录,我为维护权利留证。如此一来,边沁所言的中心瞭望塔不再是“权力”的唯我独尊,每一个拿着手机的拍摄者,都可能成为中间的凝视者,成为具备一定话语决断力的主体。
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监控能力,“权力坠落民间”似乎成为民主发展进程中的普遍风景。由此,权力的绝对垄断不复存在,权力的弥散随处可见。“我都拍了,我不明真相?你懂还是我懂?”
将心比心,就像人与人的相处要有合适距离,警民之间本身也需要“安全距离”。所谓的安全距离,大概是“既感觉被保护又不感到被侵入”。一定程度上,摄像头也是彼此警惕丈量的“尺子”。但摸准这样的分寸并非易事。过于膨大的警权让人担心出现“警察国家”,但如果警权过弱,安全感就能保证?
正因此,面对“警民互拍”,舆论并非一边倒叫好。有人说,警察在本质上是国家暴力机器,不可能“春风十里不如你”般温柔;有人甚至担心,警察如果执行保密行动,也能随意拍?被人随意截取视频,标题党了又怎么办?
一篇名为《请公安部的老爷们去一线执勤》的文章,似乎又将基层警察的怨言置顶到了舆论面前。的确,基层警察在执勤中,被辱骂殴打已不鲜见。他们甚至“羡慕”美国警察的“霸气”。透过对工作辛苦的抱怨,其实不难看到:这也是对权力折价的失落。
警权屡屡失信,警民“剑拔弩张”。如果从“权力垄断”的视角,我们很难想象公安部会允许围观者堂而皇之地拍摄;但如果一概阻止拍摄,难免执法公信力会继续走低,警察光有“权力”,没有“权威”,又有何用?
重建权威,已不能再等。其实,规范执法、专业执法从来都是老调而非新曲,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文件到了基层,扭曲变形走样所在多有。如果高层的权力之手无法掌控具体的执法情境,那么引入第三方拍摄也就引入了监督的“鞭子”。如果镜头之下,警察能谋其政,也重获应有的尊严;公众能尽到义务,同时被更好地尊重,那么“退半步”,未尝不是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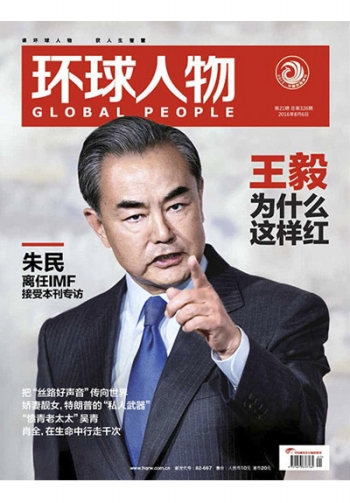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