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届香港书展近期举行,首次以“武侠文学”为主题,并专设“笔生武艺——香港的武侠文学”展览,共8位作家入选:梁羽生、金庸、古龙、倪匡、温瑞安、黄易、乔靖夫及郑丰。
我是资深武侠小说读者,不过在这8位武侠作者中,我只熟悉前5位。如今我也很少看武侠小说了,只偶尔复习一下古龙的书。古龙的武侠小说虽有单薄、浮夸之弊,又常偷师日本作家,但其风格冷峻、想象奇崛,有浪子之气、赤子之心,至今我仍觉不坏。至于梁羽生,我视之为迂儒;金庸,被过度崇拜的作家、世故老人;倪匡,主要是编剧而非小说家;温瑞安,早年山寨古龙,中年以后山寨自己;黄易,穿越之祖,与武侠关系不大;乔靖夫与郑丰,我未读过,不能评论。
武侠文学已式微多年。在无人驾驶和虚拟现实(VR)技术风行的时代,鲜衣怒马的多情剑客注定不合时宜。更重要的是,武侠所对应的老派精神,在人们不断追逐新潮又被新潮吞噬的当代,也早消亡。
说到老派精神,我最爱邵氏武侠电影,《独臂刀》《大醉侠》《月夜斩》《流星·蝴蝶·剑》《刺马》……古道西风瘦马的外景,亭台楼榭小桥流水的内景,或苍凉或雅致;豪侠在酒楼上狂歌痛饮,再鏖战一番,又或于驿道荒野对决,盘肠大战;刀光剑影中不乏红粉佳人的眼波,壮士慷慨赴死之前也必有番儿女情长。
那时的特技不多,动作也不华丽,但简单、直接、刚劲,让人如临其境;那时的武侠更重情节,往往一波三折,动人心魄;那时的武侠也重对白,只言片语之间,就把人物性格用利刃刻出;那时的武侠,就如同春秋战国的游侠,不动声色,但随时可以锐身赴难,风萧萧兮易水寒。如今的武侠,更像是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身手不凡,但挤眉弄眼,英雄无处觅肝胆。邵氏武侠拍得奇快,平均质量却颇高,我常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动不动斥资上亿、费时数年的武侠片,却难及邵氏武侠的十一。
若要为武侠招魂,须先论其源。略考之,古之侠者实起于战国,成于秦汉。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者的法就是道义,以平民的道德契约与任侠精神对抗庙堂礼法,不惜杀身成仁,虽万千人吾往矣。相对儒之精英,侠士更多平民意味。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赞美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又将其分为“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与“匹夫之侠”三种,无论哪种,都在强调侠的平民身份。
时光流转,平民之侠在当今之世已很难复兴,但仍有其独特精神价值。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将侠义精神归结为“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可谓精当。倘若浊世横流,强权者上下其手肆无忌惮,大人先生神州袖手甚至同流合污,就更应唤起一些平民任侠的精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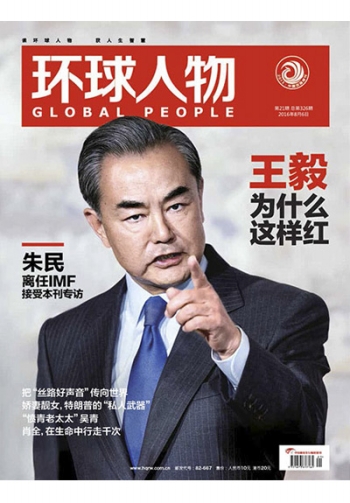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