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南京的天气还很炎热。《环球人物》记者刚下火车,就给70多岁的戴澄东老先生发了短信。半小时后,记者赶到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江苏省统战部。谁知老人早已等在那里,一见记者便招呼:“这么大老远的,辛苦了。”
戴澄东是戴安澜最小的儿子。他1岁时,戴安澜牺牲于缅甸茅邦。长大后,戴澄东常读父亲的日记,上面写着:“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而更多关于父亲的故事,他都是从长辈们那里听来的。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我的父亲是抗日英雄戴安澜,我一直为此骄傲。父亲曾在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1933年,父亲29岁,日军进军热河,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长城抗战打响。父亲从南方赶来,参加了古北口战役,任17军25师145团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父亲先后率部参加了保定、漕河、台儿庄和中条山等战役。1938年5月,因屡立战功,他被提拔为第85军第89师副师长。次年1月,又升任第5军第200师师长。
父亲曾率第200师出征缅甸,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师。在出征缅甸的关键性战役中,父亲取得了胜利,全师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父亲也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而盟军对他也赞赏有加。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评价父亲说:“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1942年,父亲在战斗中负伤,殉职缅甸。第二年3月,父亲的追悼会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前举行。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在悼词中说:“戴故师长为国殉职,其身虽死,精神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重庆的蒋介石也献挽联一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毛泽东也在延安为父亲作诗,写下《五律·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你一定愿意要英雄父亲”
父亲1904年生于安徽无为。小时候读过些书。父亲原名戴炳阳,1924年大革命爆发,他投奔国民革命军,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当时,祖国正处于危难中,父亲十分难过,为“镇狂飙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改名字叫“安澜”。
1926年,父亲与自小定亲的母亲在广州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成了家。婚后,养育我们兄弟姐妹4个。1928年大哥满月时,父亲陪母亲去照相馆拍照。其中有一张父亲的单人照母亲一直带在身边,刚识字的母亲还在背面写下“亲爱的澜哥哥”。
在母亲眼中,父亲是个善战的军人。父亲曾跟母亲说过在前线作战的细节,他们常准备一桶凉水放在身旁,枪打热了,就放进去降温。寄回来的家书中,父亲总提到今日大捷的消息。母亲就认为,父亲是不会打败仗的。
在哥哥姐姐的记忆中,父亲在军队训练时,声音很大,大家都怕他。但回家后,却很少说话。父亲平常喜欢看书,不管行军打仗多累,回家后都会安安静静读书。
在部队,父亲同样没停止学习。他跟大学生学几何、练英语。在日记中,父亲写道:即便在炮火连天的日子,也要求得知识的丰富。日记中有70%的内容记录了他的学习成果。后来,父亲带远征军作战时,已经能和英国人用英语交谈了。有一次,父亲去缅甸眉苗开会,迷路了。两辆小轿车打他跟前过,父亲挥手拦下,大概问了一句:“Where is Meimiao(眉苗在哪里)?”坐在副驾上的人刚好认识父亲,说:“老戴你疯啦,这是委员长的车。”父亲一看,里头是来缅甸战场视察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父亲在前线,总会记挂着母亲和我们。他曾遥寄家书说:“篱儿(姐姐戴藩篱)要买皮鞋,是不成问题,现在还在打仗,无市场可买,稍迟再买来给她。”四处的征战,常让他与我们聚多离少。哥哥告诉我,父亲曾跟他说:“你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但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愿意要英雄父亲。”
“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
大革命那几年国内混战,父亲在广州,后来参加北伐。1928年,他亲历了日本人制造的济南惨案,决心要与日寇拼杀到底。
有人说,与其他将领相比,父亲是更纯粹的军人,他是国民党将领,但对国共合作、全民团结抗战的支持是无私的。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当听说八路军在一次战斗中给了日军沉重打击,他写下:“抵抗日寇必然是前方与后方两个战场一起之努力,中国之抗战必然是全民族之抗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英美的一再要求下,中国组建远征军,父亲受命率第200师征战缅甸。蒋介石曾单独召见父亲,询问在日军进攻的重镇东瓜,第200师能否坚守一两周,打胜仗?父亲立下军令状:“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战前,父亲立下遗嘱:“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之后,父亲率领部队同4倍于己的日军苦战12日,成功掩护英军撤退,歼敌5000余人,东瓜保卫战大胜。
1942年4月21日,父亲又奉命收复东瓜以北的棠吉,大批日军由泰国、老挝边境窜至中国军队后方围攻,第200师陷入重围,上级急令其突围回国。5月18日,父亲率部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过公路时遇敌人伏击。大炮轰鸣,敌军的机关枪一阵扫射,父亲中了4枪,胸部、腹部各两枪。这4枪都没打中父亲要害,如果有药品医治是不会致命的。父亲顾不上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全师向缅北撤退。几天后,伤口都生了蛆。5月底,父亲的担架被抬进缅北茅邦村山上的一座小庙。598团团长请示部队该从何地退回祖国,父亲已说不出话了,他指指地图上的瑞丽,示意部队在此过境回云南。随后,父亲朝北向祖国看了一眼,便与世长辞了,年仅38岁。
父亲牺牲的消息电传回国内,蒋介石命令一定要将遗体抬回来。缅甸天气炎热潮湿,过了两三日父亲的尸体开始腐烂,只得在中途火化,用木板做成简易棺材,装敛了骨灰,沿着滇缅公路向北抬运。
“国家没有忘记抗日英雄”
父亲牺牲的时候,哥哥还在读中学。那天,他正在学校玩双杠,高年级的同学走过来问:“你爸爸是戴安澜?”“是。”“死了。”哥哥听到手一滑,从双杠上摔了下来。回家后,母亲已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两个人抱头痛哭。母亲曾收到父亲从前线寄回的“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家书,但真正面对父亲的死讯,还是没法接受。迎接父亲棺木时,母亲哭得撕心裂肺,一定要开棺见人,几个抬棺木的士兵劝了好一阵子,说“公殡过了才能开”,母亲才作罢。
家里没了主心骨,母亲很消沉、也不想活了,后来才慢慢坚强起来。小时候,我们一家人过得很苦,炒菜放很少的油,冬天穿着单裤。父亲生前节俭,除了几件好点的衣裳,什么也没留下。即便如此,国民政府给的20万元特别抚恤金,母亲还是全捐给了戴安澜高级技术学校,作为办校经费。为了生计,母亲带着我们耕地种菜、种棉花学纺织,很是辛劳。她还要照顾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奶奶、叔叔和姑姑,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父亲牺牲后,我们住在贵阳,而父亲的棺木一直在广西。后来日本人打到广西,我们将父亲的棺木迁到贵阳。抗战胜利两年后,母亲带我们去了南京,又多次找政府,终于将父亲的棺木运回家乡,安葬在芜湖赭山北面,坐朝长江和故乡无为县。国民党退败台湾前夕,有人找到母亲,希望我们全家能去台湾。母亲拒绝了,她说:“安澜葬在哪里,家人就要一辈子守在哪里。”
很多年后,母亲还是常常提起父亲,她总唠叨:“几十年了,你父亲连个梦都没有托给我。”母亲说,父亲的魂还在缅甸,他牺牲的那座寺庙里。1971年,母亲去世,和父亲葬在了一起,但她的心愿成了我的心事。2007年我退休了,就想着要去父亲牺牲的茅邦村祭拜,把父亲的灵魂迎回来。
2011年,我去了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坑坑洼洼的土路,行走十分不易。我很难想象,父亲与战士们行军打仗,要经历怎样的苦难。如今,茅邦村已被废弃,寺庙只剩墙基痕迹。我拿出手抄的《陀罗尼经》焚烧,跪在地上祭拜起来。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一位当地人告诉我,灵魂不能暴露在太阳下,这是你父亲来与你相认了。
这次前在缅甸,我还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东瓜、棠吉。有一座碑上刻着“中国远征军纪念碑”8个字,据说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仅剩下这一座。我想在父亲牺牲的地方建一座第20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一份战士名单。当年赴缅作战有9000名官兵,死伤5000名,名单上却只有56个人的名字。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举行了盛大阅兵,很多老兵受邀参加,我姐姐戴藩篱也坐在参阅敞篷车上。她跟我说:“国家没有忘记抗日英雄,我们为父亲,也为更多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先烈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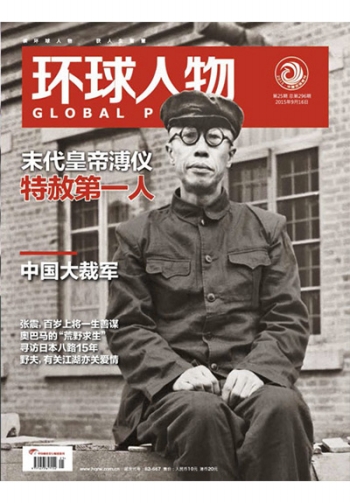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