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历史与我的瞬间》等。
梁鸿有股干练爽利的劲儿,一阵风似的走到《环球人物》记者跟前,高筒靴,围巾随意搭在胸前,一条长项链摇曳其间。采访临时改在了咖啡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落座。如果说谈一个问题分几个层次是学者惯常的思考方式,她还有种跳脱出个人情感的反省精神。这种掰开了、揉碎了的背后有一种对生活的细微体察以及自信。
她因书写家乡梁庄而广为人知,也会感叹跳不出“故乡”这个窠臼,她也曾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庄之于梁鸿,是一种情感,也是观察社会的切口,更是一个个体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在物理意义上,她的确离梁庄而去;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梁庄仍旧是她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三个女孩的命运
对于一个农村女孩而言,菊秀、霞子、梁鸿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生活形态。贩橘子、帮砖厂拉工人、开麻将馆……菊秀不得不过着她曾经嫌弃的庸俗生活;霞子考上了师范学院,在小镇上当老师;大学老师梁鸿,买书成癖,看芭蕾舞剧《浮士德》,参加诗歌朗诵会。
三人是儿时好友,都对未来怀着理想和憧憬。梁鸿说:“每个青年都是文学青年,这是青春特有的。但能否留下来成为真正的爱好,还要经过无数的考验。”她生在河南邓州,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以及一个妹妹,母亲多病,父亲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考师范,到乡下教书,然后一路进修。
这个曾天天写日记的女孩梦想着成为作家,但她对风花雪月、心灵鸡汤保持着一种警惕,因为那“对一个人的思考来说是有限的”。她更像一个冷静的思考者,“我希望自己对事物有思考,有多方面的看法。”说到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她说:“我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父亲的影响也不是完全积极的,我没有楷模。”在谈到理想时,她说:“理想情怀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绊脚石,是个普遍的状态,因为生活会压抑我们的理想。尤其对一个普通农村孩子来说,理想主义更不好,我属于侥幸的。但大部分怀揣理想的青年在乡村底层挣扎,并且可能会生活得更艰难,就像菊秀。”
“理想本身是好的,我讲的是通道问题。没有了上升渠道,你所有的理想都变成了毒药。一旦成为农民,你就不能抱着理想了,甚至连一般的诗情画意都达不到,因为你的道路非常窄,你的理想也许就变成可笑的东西了。”说这话时,她面前拿铁咖啡上的奶泡正渐渐模糊。“一个城市小青年可这样坐着喝个咖啡,但要是个农民进来喝咖啡,你就会觉得怪怪的。但农民为什么不能喝咖啡?!因为社会没有给他提供这个空间,他只能疲于奔命去挣钱。”
一个村庄30年的变迁
博士毕业从事了几年研究后,梁鸿越来越觉得苦闷,“离创作远了,研究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向。”她称之为“精神的困顿”,其实,这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问题。“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这并不是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很有道理,但一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可笑与苍白之处。”
2008年暑假,她回到故乡梁庄,听留守的人们讲自己的故事以及乡村的故事;她又到西安、南阳、广州、青岛、郑州、厦门、深圳等地,采访了340多名外出打工者。一个村庄30年的变迁,以及打工农民在城市的寄居生活展现在她的眼前……
乡村修起了路、建起了楼,但小学被废弃成了猪圈,曾经洗澡、捉鱼的母亲河湍水被污染了,曾经的权力中心——老支书的家仍旧停滞在上世纪70年代的模样。五奶奶11岁的孙子被淹死了,芝婶也在担忧孙子的教育问题;留守的王家少年白净内向,却强奸并杀害了82岁的老太太;在外做生意、颇有前瞻性的焕嫂子在生了7个女儿后,仍旧想生个儿子……曾经的家园正在失去,曾经的礼俗、道德也在逐渐失去。
同时,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西安蹬三轮的万国、万立兄弟为了“一块钱的尊严”打架;娶了城里媳妇的贤生,把兄弟姐妹带到了南阳,在城中村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住了25年,然后埋回了梁庄;青焕姑奶在北京打工被车撞了,她丈夫觉得判得不公,每周五法官接待日都要去讨说法;重点大学毕业的梁磊在深圳的公司工作,和怀孕的妻子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楼,依旧看不到未来……那些发财传说被无情捅破了,城市的生活依然艰辛。即便是生活得很好的人,比如朝侠,她的关系中心仍然是梁庄这帮亲戚和老乡,他们与所在的城市仍旧是隔膜的。
相比于这些故事在社会引起的反响,这些鲜活故事的当事人对此知之甚少,这对他们根本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感触最多的可能还是梁鸿,“这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艰难历程,因为你突然发现,你对他们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一天下午,她的哥哥和她说起在北京打工时,怎样被当做倒票的收容遣返,怎样被卖到黑砖窑,后来又怎样逃跑,差点把命丢掉。“这种生活内部的隔离,是非常正常的,哪怕是亲人你都不知道他是如何生活的。但他为什么被遣返,为什么被卖到黑砖窑,这不单单是个人命运,背后蕴含着社会矛盾。”
多一点软弱和疼痛
在某种程度上,梁鸿是个精神至上者。她重返乡村是因为精神上的困顿;而重返之后,无论是乡村留守者还是进城打工者,让她最痛心的仍旧是他们精神上的困境。“在农村,一个是‘新生’,一个是‘废墟’。‘新生’是经济的新生,道路的新生,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情感和文化的废墟状态。尤其是孝道,在农村已衰落到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了。这一状况所产生的原因又非常复杂,与整个时代精神的堕落、生活的分离、成功学法则、乡村道德结构的破产都有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伦理的衰退。”
作为旁观者和书写者的梁鸿也热心参加一些乡村建设的公益活动。“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乡村实践方式出现、生长,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这并不重要。实践的过程更重要,它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可能性,不只有朝城市飞奔这一种可能性。”
乡村该向何处去?对于城镇化这个国家策略,一向理性的梁鸿倒是主张多点多愁善感。“在讲城镇化高速运行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恰恰缺失一种情感性的东西。可以少一点坚硬,多一点软弱和疼痛。有疼痛才有尊重,有尊重才有敬畏,有敬畏才可能以善良而平等的心去面对他人和这个时代。今天我们太缺乏多愁善感了,太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对个体情感和生命感受的尊重了,以发展之名,我们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人,最终,失去一颗能够体会家、爱、尊严和情感的心灵。”
一名学者的无用之用
从2008年返乡,到2010年出版《中国在梁庄》,再到2013年出版《出梁庄记》,5年时间,梁鸿一直写梁庄,每次出行和归来,她都在体会一种巨大的落差。“从破旧的、有着发霉味道的出租屋回到自己的家,洗个热水澡,听着音乐,当然很舒服了。但是你要警惕这种舒服,因为你面对着本来不应该有的巨大的差异,要促进自己去思考。我在青岛考察时,住在一个叔叔家,屋里是泥巴地,一进去就闻到巨大的霉味。当时我特想逃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状况你不愿面对,这恰恰说明巨大的差距横亘在我们生活之间。”
写完梁庄之后,梁鸿内心一直有种失落。“从广泛意义来讲,我描述的,并不是光鲜的、欢欣鼓舞的,而是一种灰色的、失败了的、让人沉重的生活。最终,你写完了,安然无恙地跳了出来,得到了名和利,但那种生活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个巨大的失败感。”那段时间,她觉得虚无而沉重,甚至有点精神分裂。
2012年年底,梁鸿又回故乡一趟,每天早晨背个水壶出去,沿着湍水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天。“你看着河流不断行进,就像历史在行进,虚无的但又充实。慢慢地,你觉得,你的书写可能没有改变什么,但你改变了你自己。同时,你能够把这种广阔的大地生活呈现出来,这本身可能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新近出版的《历史与我的瞬间》里,她那种纠结终于释然了。
前不久,梁鸿在国家图书馆做讲座。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个农村妇女站起来说,她春节回老家,看到一个老头仅有一块钱,想上公交车,但那个车要3块钱,结果老头又下去了。回想起来,她特别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懦弱,为什么没有给他补上那两块钱。这个有点琐碎的故事令现场有些人不满:这种事就别说了,提问题。
但梁鸿听了非常感动,“我们对这种生活有了某种共同的理解。”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微乎其微的,我写梁庄到底有什么用,可能是无用之用。它没什么用,但有人看到了会思考,有感触。”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名学者的梁鸿看到了无用之用对于改变社会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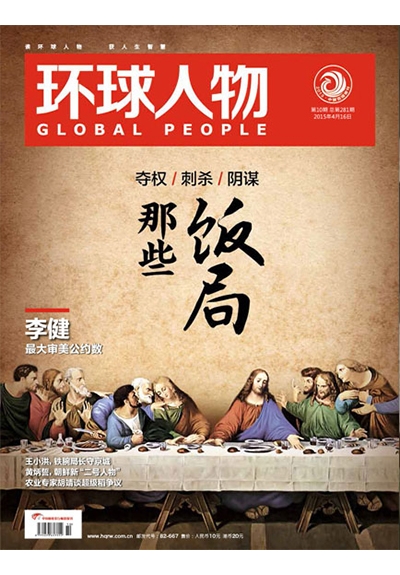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