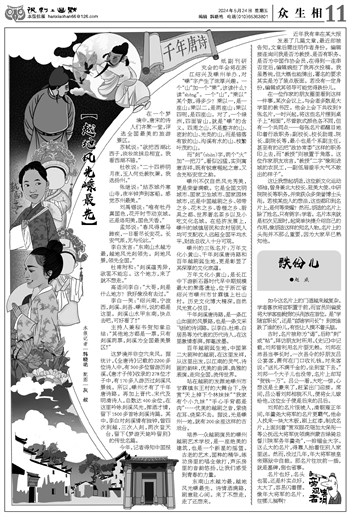近年我有幸在某大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最近却被告知,文章后需注明作者身份。编辑接连询问我是否为教授、是否有职务、是否为中国作协会员,在得到一连串否定后,编辑婉拒了我再次投稿。我虽愚钝,但大概也能猜出,署名的要求其实是为了装点版面。若没有一定身份,编辑或其领导可能觉得跌份儿。
在一位作家的朋友圈里看到这样一件事,某次会议上,与会者多数是大学里的教书匠。他会上会下共收到9张名片,一时兴起,将这些名片摆到桌子上“相面”,尽管款式颜色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每张名片都醒目地印着行政职务:副校长、校长助理、院长、副院长等,最小也是个系副主任,甚至有的还把“政协常委”这样的职务印上去,而“教授”则被置于角落。这位作家朋友戏言,“教授”二字“像刚进城的农民工,一副低眉垂手大气不敢出的样子”。
这让我想起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曾身兼北大校长、驻美大使、中研院院长等职务,并荣获众多荣誉博士头衔。若按某些人的想法,这些都印到名片上,是何等荣耀?然而,胡适的名片上除了姓名,只有俩字:学者。名片本来就是初次见面时,起简单快捷介绍自己的作用,像胡适这样的知名人物,名片上的头衔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大家早已熟知他。
如今这名片上的门道越来越复杂,学者喜欢将官职置于前,而官员则偏爱将大学客座教授的头衔放在首位。是“学随官职长”,还是“官随学问长”?到底谁跌了谁的份儿,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古时,名片被称为“谒”,后称“刺”或“帖”,拜访朋友时所用。《史记》中记载,刘邦曾利用名片耍无赖。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宴客,萧何在门口收礼钱,对来客说:“送礼不满千金的,坐到堂下去。”刘邦一个大子儿也没带,名片上却写“贺钱一万”。吕公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这是土豪来了,赶紧出门迎接。席间,吕公看刘邦相貌不凡,便将女儿嫁给他,这位女子便是后来的吕后。
刘邦的名片很唬人,清朝雍正年间,年羹尧大将军的名片更霸气,他命人找来一块大木板,刷上红漆,制成名片,上面刻着“赏双眼花翎加太保衔一等公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骑总督川陕军务年羹尧”,一排镏金大字。这么大的名片,得靠人抬着往别人家里送。然而,没过几年,年大将军被皇帝赐狱中自裁。那名片往坟前一插,就是墓碑,倒也省事。
名片也好,名头也罢,还是朴实点好,太大了,容易闪着腰。像年大将军的名片,往哪儿搁啊?